相比Boston Legal,我更喜欢the Practice。
前者太过宣扬主角的个人魅力,使我们沉浸在Alan的滔滔雄辩和Denny的玩世不恭中,几乎每一集的结局都是英雄般的胜利,听见陪审团裁决“not
guilty”。而后者,经常把一些“令人沮丧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郁闷无比。
第八季第十一集,Joe曾经讲过这个故事,我再讲一遍。
深夜,一名警官中弹身亡,同伴并未看见何人开枪,只见一人撒腿狂奔,便紧紧追赶,最终将其击伤擒获,但未寻获凶器,亦无任何其它证据;据嫌犯同伴说,他们刚从酒吧出来,听见枪响,嫌犯担心被抓到违反十点以后不得出门的假释条例,就拔腿逃跑。
警官们义愤填膺,把医生赶出病房,对受伤的嫌犯百般折磨逼供,律所的五名律师一名助理全数到场也毫无办法。实际上,检察官很清楚控方证据不足,而只有在口供上做文章,而他们需要绕开美国法上的“毒树之果”原则(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用于指证嫌犯)。于是检察官取得嫌犯供词,指证其同伴为凶手,由于并非对嫌犯不利的证据,因此在技术上有效;随后利用此份证据威逼嫌犯的同伴,在未受刑讯的条件下指证嫌犯为凶手,以此份证据指控嫌犯,由此洗清证据上的“毒素”。
律师随即提出动议要求立即驳回指控,在庭上慷慨陈辞,而聆讯法官对检察官的做法也深恶痛绝,但细细查考法条判例,竟无法否定经过清洗的证据,而只得允许案件进入庭审。检察官随即提出辩诉交易,以非法枪击的轻罪罪名、建议量刑六个月,被告无奈,权衡之下只得接受。
整个案件令人郁闷的是,实际上最后所有的人都输了。警官身亡,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无辜的被告接受刑罚,律师的信念遭到极大挫折,法官不得不忍受令人恶心的刑讯所获得的证据,检察官只是把一只替罪羊送进监牢。
我相信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编剧凭空杜撰,对人权和自由如此重视的美国,尚且会发生如此的情况,我们又当如何。尤金在庭上大声疾呼,我们不能放任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不能容忍践踏人权的恶行;当大家觉得疲倦的时候,尤金激动地拍桌子:各位,我们都上过法学院,这就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案子!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在法学院里学到的,是捍卫公平正义、保障人权自由的信念。最后被告无奈地接受交易,尤金一个人在黑暗的办公室里抱着头,我想他对于正义的信心已经动摇;埃莉诺进来说:我最担心的是你那种无助的眼神,这个法律系统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不放弃。
我想到杨佳案。杨佳最初被警察拦下盘查,后来遭到殴打的时候,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赤裸裸地暴露在警察权力之下,没有律师、没有权利、没有保护。他要报复,因为从朴素的感情出发,对不正义的纠正,就是报复,于是他杀了六名警察,当检察官在法庭上问他,那六名警察难道不是无辜的吗,他回答说,他们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是警察权力的持有人,如果我们回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初期,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责任”的概念,一人犯罪,同族受罚,所以,作为一个群体,这些警察就不是无辜的。
杨佳的血腥报复,确实是本人的犯罪;但是,从报复正义的角度出发,是报复过当,如果我们假设杨佳只是在闸北警察局的那位督察下班回家途中把他拦下殴打一顿,我们会如何看待?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现在判处杨佳死刑,同样也是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护,没有什么进步,下一次警察殴打嫌疑人,如果碰上一个抱有原始社会报复观念的二楞子,还是会发生同样的案件。
我们全体沉默。在杨佳被警察殴打的时候,法律沉默着,我们所有人都沉默着,我们的宪法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我们的法官从来都服从权力者的意志,我们的律师则噤若寒蝉、不会也不可能在法庭上为人权和自由像尤金那样感到热血沸腾。我完全不是要为杨佳辩护,按现行法律他应该被判死刑,网上流传着一份多位学者名人签署的要求特赦杨佳的请愿书,我认为实在是一场无聊的做秀。实际上,杨佳本人也没想过要活命,他在上诉状中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改判之类的要求。我信任翟建律师,而他在二审中能做的也只有提出重做精神鉴定的请求。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郁闷,我们如此沉默?法官在庭上说,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未来可能生活在一个滥用权力的警察国家,就觉得不寒而栗。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担心吗?我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也会想,我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多少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警察权力的伤害,而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就掌握这种权力。不过,请注意,这样一种权力是需要通过伤害别人来揭示自己的存在的,它不是消极自由,不是free from,而是free to;当人们普遍陷入一种对权力的争夺后,即便是掌握权力的人,也无法免除权力的伤害——一种对心灵的毒害。
我没有从事律师职业,因为我和Alan一样,认为那是个ugly
business,我逃开了,不愿意参与其中;或者,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从事这个行业,正义感很有可能会迫使自己被消灭(我觉得消灭比沉沦的可能性大一些),于是我怯懦了,沉默地逃开?
我们不如美国,我们是一个警察国家,当好人们沉默的时候,灾祸就不远了;我们不能放弃,正义不允许好人放弃,我们的希望不在别的地方,在于自己的内心。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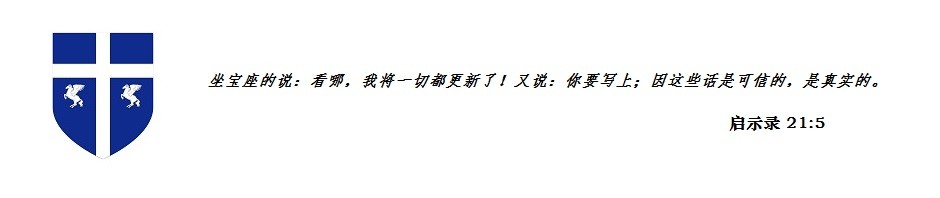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倒数第二段,所谓“我们”,也许可以甄别一下主体并且明确的对应。
望主能救我的内心,也能救我去还有主,主尚未遗弃的地方。
想起十年前到华政面试,考官问我为什么想读法律,我答曰想主持正义。一直记得他的眼神,直觉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答案。
看了评论,感到不值得评论。我希望你谈一谈“三鹿事件”的当事人,该如何判、能如何判、会如何判。有难度吗?
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哈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