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如茵芳草
伦敦城外,希思罗国际机场西面的泰晤士河边,有一片草地,在那里已经许多许多年,并未改造开发成办公区、住宅区或者什么旅游区。从沿河岸的温莎路拐上一条小路,就可以一直通向大宪章纪念碑。人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小亭子,竖起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纪念大宪章,法律下的自由的象征”。在这个纪念碑的不远处,还有一个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纪念碑。
主后1215年6月15日,清晨,英格兰国王约翰带领仍然忠于他的大臣和侍从们来到泰晤士河边的兰尼米德。他的营地在西边的温莎,而反叛的男爵们带领大军驻扎在东边的斯泰恩斯,位于温莎和斯泰恩斯之间的兰尼米德,看起来是一个谈判的好地方。
尽管约翰国王保持着高贵的皇家风范,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如果不接受男爵们提出的条款,必将兵戎相见,而这场战斗必将以国王的失败而告终。尽管约翰当政以后,心存不满的贵族也曾有几次企图阴谋造反,但无一例外地
遭到国王强力镇压;现在,时过境迁,反叛者声势浩大,支持国王的寥寥无几,并且,国王的手中没有可以抵抗的军队。
事情要慢慢说起来——
1214年是个多事之秋。此前一年,约翰刚刚解决了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端,向教皇屈服,将英格兰全地奉上交与教会,再作为封臣受封于教皇,以此阻止宿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入侵,同时解除教皇对英格兰实施的禁教令,恢复全国的宗教活动。但是在短暂的蜜月期后,国王与前来就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约翰通过走教皇的上层路线,暂时压制了大主教。不过比起大陆上的战事,与大主教之间的争端看起来只是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
金雀花王朝的约翰,他的父亲是文韬武略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母亲是中世纪的传奇女性之一阿基坦的埃莉诺,他的兄长则是十字军伟大的英雄、“骑士之花”理查德一世。1199年理查德在一场围城战中为弩箭所伤,不久辞世,约翰即位。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衙内不得不接过父兄留下的基业,独自担起金雀花王朝,而他面对的最大敌人则是一生以颠覆金雀花王朝为己任的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
到1205年,约翰丢失了父兄留给他的大部分欧洲大陆领土,连征服者威廉发家的基地诺曼底也陷入法国人手中。约翰可能是一个骄纵、暴戾的国王,但是在领土问题上并不是没心没肺的,他非常想夺回大陆领土,因为丧失父兄辛辛苦苦创业得来的成果,实在是件叫人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约翰谋划了一个相对长期的反攻大陆计划。1214年这个计划进入最后的实施阶段,约翰通过金钱和关系纠集起一个反法联盟,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奥托四世(他的侄子)、弗兰德斯伯爵等人,各方约定兵分几路同时进攻法国,想要一举摧毁腓力二世。不过运气并没有站在约翰这边,布汶一役北线的反法联军大败,奥托四世从战场上仓皇逃回本国,英军统帅索利斯伯里伯爵长剑威廉(约翰的私生子哥哥)、弗兰德斯伯爵费尔兰以及布伦伯爵雷吉纳德被俘。约翰无奈,与腓力二世签下停战和约,撤回英格兰。
1214年10月15日,约翰国王回到英格兰,经年煞费苦心构建起来的联盟被击破,主要盟友不是逃走就是被俘,更重要的是,数年间狠命搜刮英格兰得来的资金血本无归——灰头土脸,人财两空。
现在国王很没有面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即便没有人逆龙鳞,也要找个理由发发彪,总之,实在是太不爽了。所以当负责税收的大司法官彼得·德·罗切向国王报告,税收任务完成得很不好的时候,约翰就要爆发了。这笔用来代替军事服役的“盾牌钱”是向那些没有跟从国王出征大陆的贵族征收的,遭到了纳税人的广泛抵制,尤其是北部的那些贵族,最后财政署仅仅收到应纳税额的四分之一。
国王很生气:一、这些混蛋拒绝跟随自己出征,似乎可以把部分战败的原因归在他们头上;二、不出工吧,还不愿出钱,拒不纳税;三、现在国王荷包干瘪、濒临破产,急需敛财;四、打了那么大的败仗回来,已经相当没有面子,这些人还继续不给面子,如此国王要往哪里搁?
男爵们的理由也不少:一、国外的战争与兄弟我们无关,不能怪兄弟不够义气,所以代替这项役务的盾牌钱也没有理由征收;二、您收去的钱有很多并没有用来打仗,而是用于政府的日常开销、结交大陆上的同盟——前次融资所得并未用于原先公告的项目,而是用来补充流动资金或者挪作他用,现在要再次融资自然不行。
这里我们就要先解释一下封建主义的原则了。
相比帝国官僚体系,封建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权宜,封建关系同时带有政治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性质。首先,封主将土地分封给封臣,以此换取封臣的军事服役(后来发展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的金钱来代替)以及其他一些义务(例如出席领主法庭的义务、发生继承时的继承金、领主被俘时的赎金、领主长子封骑士及长女出嫁时的辅助金等);其次,封土范围内的管理责任也将由封臣承担,他必须负责地方上的治安、司法以及文教等义务;此外,封臣往往需要对封主行效忠礼,二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人身关系,封臣对封主效忠,封主则有义务保护封臣不受他人伤害,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在这种层层契约的架构下,社会实现了稳定和安全。
在这种体系下,理论上讲,封臣们并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一种类似占有的“保有”,而封建保有关系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而各有不同。
因此,反叛男爵们提出的理由,实际上在封建主义原则下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首先,约翰的父兄,前二任的英格兰国王,在英格兰境外用兵绝不在约翰之下,亨利二世长年在大陆与法国征战,而理查德则参加十字军远征圣地。其次,亲自服役、提供骑士服役还是支付盾牌金的决定权并不在封臣手中,而是由封主决定的。
所以,在约翰看来,拒绝跟随国王前往法国作战已经是大逆不道,属于先行违约,凭此就可以解除封建契约,收回分封的土地。但是,这些贵族们实在也已经忍受了很久。因为约翰一心要收复大陆领土,数年间横征暴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榨取封臣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有反叛的男爵与约翰之间的仇恨,几乎都是个人性的,都是因为某次特定的事件对国王大有怨恨,而不是出于约翰违反某项总的封建法律或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此次贵族们如此团结而有决心。约翰战败归来,声望跌落到谷底,没有稳定局势韬晦一阵,却高调地征收每骑士领三马克的重税,自然一下就激起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应。
11月20日是圣埃德蒙节,男爵们以庆祝宗教节日为名聚集到圣埃德蒙修道院商议对策,这里埋葬着英格兰伟大的殉道者,其地位不亚于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大教堂。几位主要的贵族首先在圣坛前宣誓,如果国王继续一意孤行、不保证他们的自由与权利,就解除效忠,向国王开战。会上可能还讨论了去年八月在圣阿尔班斯会议上坎特伯雷大主教朗顿提出的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词,研读誓词后,男爵们受到了相当大的鼓舞。最后全体与会者同意,圣诞节以后,定要面见国王主张权利,并且带上各自的军队,如果要求不得满足,马上开战。
约翰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机,他首先想到的对策是分化瓦解他的敌人。11月1日万圣节(All Saint’s Day),他向大主教和主教们支付了议定的与教皇纷争期间教产损失的部分赔偿金六千马克;11月21日,国王又发布一项特许状,确保英格兰教会的自由选举权,这是对已经长久不再实践的英格兰教会传统的确认。
约翰在沃切斯特过了圣诞节,但是完全没有过节的心情,只呆了一天,立即动身前往伦敦的圣殿(圣殿骑士团英格兰分舵所在地)。男爵们相约而来面见国王,带领着全副武装部队,盔明甲亮、气势汹汹。男爵们要求约翰“恢复爱德华国王的良好法律”,遵守自己1213年在温切斯特接受教皇赦免时所作的誓言。约翰眼见形势不妙,也不计较男爵们言语不敬,只得使一个拖字诀,告诉男爵们兹事体大,需要慢慢商议,等到复活节过后的4月26日再作决定。男爵们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满足,双方在圣殿交涉许久,最后国王无奈,只得请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伊利主教尤斯塔斯和大家公认的骑士典范威廉·马歇尔从中作保,男爵们才引兵退去。
形势越来越紧张。1月15日,约翰再次发布特许状,进一步确认教会的选举自由,承诺无论习惯如何,教会都享有完全的自由选举权,同时将特许状送往罗马请教皇英诺森三世加以确认。随后,约翰要求全国封臣重新向国王行效忠礼。2月2日,圣烛节,约翰宣布起誓参加十字军,如此在理论上就没有人可以对他动武。3月30日,教皇回函确认了此前送去的特许状。
国王的这一系列动作虽然可称迅速,但是所表现的已经不是灵活的政治手段,而是一种后背发凉的恐惧感了。4月29日,约翰把幼子理查德送往好友彼得·德·莫莱处,托付他善加管教。
复活节期间,4月19-26日,男爵们在斯坦福集结,军力包括两千名骑士,此外还有大量骑兵、步兵和附属人员。叛军的主要领袖包括:
罗伯特·菲茨–沃尔特(Robert Fitz-Walter),此公祖上是跟随征服者威廉而来的诺曼贵族,当时已是英格兰巨富之一,常年从事贸易,他的葡萄酒货船享有国王授予的特许权。他的妻子龚娜是北方世家之女,婚姻也为他带来了至少三十个骑士领。罗伯特曾经在诺曼底担任沃德里尔总督,1203年腓力二世进攻诺曼底时,此人未作任何抵抗主动投降。1212年约翰查办叛乱阴谋,要求各地贵族提供人质,罗伯特闻讯立即逃往法国,后来与逃亡至法国的主教们会合。约翰与教皇和解后,罗伯特随同主教们一起回到英格兰,作为和解的条件之一,约翰向罗伯特归还了原来的领地。他是约翰的宿敌之一,并且始终与法国有良好的关系。
尤斯塔斯·德·维希(Eustace de Vesey),罗伯特的密友。他的妻子是苏格兰国王雄狮威廉的一个私生女,所以与苏格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曾经调停促成了1200年威廉向约翰的效忠。在罗伯特逃往法国的同时,尤斯塔斯逃往苏格兰避难,他回国的情形与罗伯特大致相同。
理查德·德·珀西(Richard de Percy),属于北方世家,布腊班特公爵戈德弗雷之孙,他的父亲约瑟林娶了珀西家族的女继承人阿格尼丝,得以接下珀西家族的产业。理查德在北方有大片的地产,他本人也是个巧取豪夺的好手。
罗伯特·德·鲁斯(Robert de Roos),同样是北方豪强。他娶了雄狮威廉的另一个私生女为妻,1200年也曾作为使节出使苏格兰。1213年约翰任命他为坎伯兰郡长,并且给予他贸易特许状。他与尤斯塔斯·德·维希的渊源很深。
萨尔·德·昆西(Saer de Quincy),温切斯特伯爵。他早年参加过1173年亨利太子对亨利二世的叛乱,此后长期穷困潦倒,直至1204年娶了莱切斯特伯爵之女为妻,后来继承了部分财产,成为温切斯特伯爵。1203年与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共同守备沃德里尔,一并不战而降。1211年至1214年间曾担任约翰的司法官,因此他加入叛乱者行列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基于与罗伯特的关系。
克莱尔伯爵理查德(Richard, earl of Clare),残存下来的诺曼贵族。理查德娶了格罗切斯特伯爵的三位继承人之一,他的女儿阿米西娅,领地进一步扩大。理查德和他的儿子吉尔伯特是当时英格兰重要的贵族之一。
罗杰·比格德(Roger Bigod),诺福克伯爵,可能也属于诺曼世家。他曾在理查德一世和约翰朝担任司法官,但后来失宠,1213年入狱,1214年随同约翰出征普瓦图,1215年再度失宠,遂加入反叛队伍。
威廉·德·莫布雷(William de Mowbray),克莱尔伯爵理查德的外甥。他是少数几位在约翰即位之初就开始整顿军备、加固城堡、准备内战的男爵之一。不过后来约翰进行了安抚,威廉行了效忠礼。
威廉·马莱(William Mallet)、威廉·德·蒙太古(William de Montacute)、威廉·德·伯香(William de Beauchamp),这三人的祖上都是跟随征服者威廉打江山的诺曼将领,因军功受封土地。1214年约翰出征普瓦图时,他们都跟随在军中,因此后来约翰征收的盾牌钱并不针对他们,可见对约翰的不满已经蔓延开来了。
小威廉·马歇尔,约翰的头号忠臣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的长子,他在名单中出现比较令人意外,因为他的父亲一直对国王忠心耿耿,后来还成为托孤重臣。小马歇尔当时还很年轻,可能受到母亲家族(克莱尔家族)这边的影响。
杰弗里·德·曼德维尔(Geoffrey de Mandeville),以及他的弟弟威廉,他们是约翰朝的重臣,前大司法官杰弗里·菲茨–彼得的儿子,杰弗里当时兼领埃塞克斯和格罗切斯特伯爵。杰弗里娶了约翰的前妻伊莎贝拉,为此支付了大笔贡金;威廉则娶了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女儿克里斯蒂娜为妻,这也许是他们反叛的原因。
约翰·德·雷希(John de Lacy),切斯特总兵。他的父亲罗杰·德·雷希当年在盖亚尔城堡抵御腓力二世的围攻达一年之久,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最后出城死战,腓力壮其为人,同意有条件投降而不杀,后来约翰支付赎金将其赎回,罗杰的忠勇一时名动欧洲。因此约翰反叛的动机不明,可能其父回国后约翰并未给予大力褒奖,反而逼迫其为封地支付大笔款项,使得这位年轻人心存怨怼。
名单上还有许多其他重要贵族,包括彼得·德·布鲁斯(Peter de Bruis)、尼古拉斯·德·斯托维尔(Nicholas de Stuteville)、罗杰·德·克雷西(Roger de Creissi)、拉努夫·菲茨–罗伯特(Ranulf Fitz-Robert)、罗伯特·德·维尔(Robert de Vere)福尔克·菲茨–沃林(Fulk Fitz-Warine)等等。
这些人中间有很多是1214年拒绝跟随约翰出征,后来被征收重税的北方贵族,但是也已经有一些中部的贵族加入,甚至有一些原本与约翰有很深渊源的人。总之,反叛声浪高涨,人数众多,军队齐整,确实够国王喝一壶的。
复活节一过,4月27日,男爵们立即出发,向南穿越北安普顿郡,到达布莱克里,距离国王驻跸的牛津已经很近了。国王获悉后,派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和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作为使节,向叛军询问他们的具体要求。男爵们开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列举他们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其中部分来源于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词,部分来自于更古老的法律与习惯。男爵们威胁说,如果国王不立即应允这些要求,就要动用武力迫使国王接受。大主教带着清单回到牛津,向约翰逐条宣读,国王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这些男爵居然提得出这些不正当的要求,怎么不说连朕的王国一并交出?他们的要求全都是徒劳和痴心妄想,没有任何合理的请求作为支持!”约翰当即发誓,永远也不会给予男爵们把国王变成奴隶的权利。朗顿和马歇尔苦劝约翰,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实在不是逞强的时候,约翰不听。二人无奈,只得向男爵们如实转达国王的态度。
这无疑就是宣战诏令,5月5日,男爵们宣布解除对国王的效忠义务,并且从达勒姆大教堂搞到一份解除誓言的教令。大家推举罗伯特·菲茨–沃尔特为统帅,号“上帝与神圣教会兵马大元帅”(Marshal of the Army of God and of Holy Church),立即北上攻击国王在北安普顿的城堡。
叛军没有强有力的攻城器械,因此围城十五天,毫无进展。罗伯特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实在不济,付出不小的伤亡后,仍然毫无收获,大元帅的旗手也被弩箭射中身亡。
与此同时,约翰当然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急召普瓦图、德文郡以及弗兰德斯雇佣军服役,准备与男爵们开战。伦敦的态度至关重要,5月9日约翰发布一份特许状,授予伦敦市民多项特权,包括每年自行选举市长的权利。另外,在5月10日国王发表公开信,要求停止敌对活动,由双方各选择四人组成仲裁委员会,另由教皇作为监督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叛军进攻北安普顿不利,转向东边的贝德福城堡,这里是威廉·德·伯香的据点,自然会受到欢迎。正在男爵们团团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传来一封改变局势的密信——“伦敦欢迎您!”如果要来,马上就来!男爵们大喜过望,立即开拔直奔伦敦。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伦敦城的市民也不是一边倒的,一些富裕的市民企图联合男爵谋求利益(后来也确实得到了),而下层的市民则敢怒不敢言,也无力阻止叛军。不过,就军事而言,以伦敦的高墙,只要关闭城门稍加抵抗,男爵们无论如何是无法进入的,北安普顿尚且攻不下来,何况伦敦。
5月24日(另一种观点认为是5月17日)清晨,男爵们带领部队接近伦敦,“开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当时正是基督升天节之前的礼拜天,市民们都在教堂举行圣事,并没有人看守城门,于是男爵们一拥而入,派兵把守各座城门、上城墙警戒,随后将市长更换为自己的亲信,只是坚固的伦敦塔仍然在国王侍卫的手中。如此一来,惴惴不安的叛军总算安定下来,并且占据相当的有利地位,因为以伦敦的坚固城墙,即便国王可以聚集起一支军队,也难以攻占。
男爵们向仍然忠于国王的贵族们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加入叛军,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战,如若不然,叛军将对他们发动攻击。被男爵们点名的贵族包括: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他的侄子约翰·马歇尔,约翰此前已将林肯郡交给他掌管;切斯特伯爵兰努夫·德·布兰德维尔(Ranulf de blundeville),1214年他在跟随国王出征的行列中,约翰也刚刚把纽卡斯尔城堡交给他掌管;索利斯伯里伯爵长剑威廉,亨利二世的私生子,英勇善战的将领;沃伦伯爵威廉(William, Earl of Warenne),约翰的表弟;奥美尔伯爵威廉·德·福斯(William de Fors, Earl of Aumale),他的父亲曾是理查德一世十字军舰队的队长之一;康沃尔伯爵亨利(Henry, Earl of Cornwall),算起来也是约翰的表弟;布兰德尔伯爵威廉·德·阿尔比尼(William de Albini, Earl of Brundel);其他如罗伯特·德·维邦(Robert de Vipont)、彼得·菲茨–休伯特(Peter
Fitz-Hubert)、亨利·德·布雷布洛克(Henry de Braibroc)、亨利·德·康西尔(Henry de Cornhulle)等人。这些人都是约翰的亲族,或者是多年的密友和近臣,尽管如此,有相当部分的人收到书信后还是倒戈加入男爵们一边,其中就有威廉·阿尔比尼。
国王看起来已经众叛亲离,据说他的身边只剩下七名骑士,即使男爵们再不会打仗,国王的城堡也已经朝不保夕,即便不是真心投降,现在也不得不做出一点屈膝的态度,表示要坐下来谈一谈。6月8日,国王签发安全通行证,请男爵们三日内派代表到斯泰恩斯进行磋商;6月10日,国王移驾到温莎,延长通行证有效期至6月15日,同时派遣忠诚的威廉·马歇尔去向叛军交涉,愿意接受男爵们的所有条件,并请男爵们确定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好吧,那就通行证有效期的最后一天,6月15日,星期一,在温莎和斯泰恩斯之间的草地,兰尼米德。
由于缺乏准确的记载,谈判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我们只能从达成的文件、前后发出的信函及令状、以及其他一些记载作些推测了。
这场谈判开始到签署最终的法律文件,一共用了五天,6月15日星期一至6月19日星期五,其后又花费数日处理文书工作等,我们知道国王一直驻扎在温莎,直到6月23日。
现在仍然存世的大宪章原件一共有四份,其中两份保存在大英博物馆,林肯和索利斯伯里的大教堂各保存有一份,实际制作的正式文件数量一定多于这个数字。现存的所有四份原本都注明签署于1215年6月15日,但是实际情况应该并不是这样。因为,首先,中世纪的文件往往标注开始制作的时间。其次,更重要的是,如此篇幅的文件在中世纪属于鸿篇巨制,就这样一份羊皮纸文件而言,在一天之内制作四份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实际的数量要远多于四份。并且,所有四份现存的文本都表现出极为精致的制作工艺,不可能是仓促之间的产品。第三,我们另外有一份“男爵条款”文件,共有49条条款,主要内容与大宪章相同,应当是一份经过谈判形成的初稿,或者是男爵们提出国王附和的初稿。这份文件上同样盖有国王的印玺,如果这份初稿是在6月15日议定,而正本也在同一天制作完毕,那么在一份将要立即产生正本的初稿上加盖国王印玺就是一种多此一举的行为,与理不太说得过去。
按当时的情况,斯塔布斯把在场的人员分为四个群体。
第一集团,是北方贵族,坚决的反叛者,他们首先发动了叛乱。这些人包括尤斯塔斯·德·维希、理查德·德·珀西、罗伯特·德·鲁斯、彼得·德·布鲁斯、约翰·德·雷希、威廉·德·莫布雷等。
第二集团,包括了剩余的同盟者,包括当年跟随征服者威廉打江山的诺曼贵族,以及新近在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朝获得土地和爵位的贵族,诸如罗伯特·菲茨–沃尔特、萨尔·德·昆西、罗杰·比格德、克莱尔伯爵理查德、杰弗里·德·曼德维尔等人。
第三集团,基本上忠于国王的贵族,大多是亲戚和密友。包括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切斯特伯爵兰努夫、索利斯伯里伯爵长剑威廉、沃伦伯爵威廉、康沃尔伯爵亨利,其他还有一些长期在财政署和王廷工作的近臣,如托马斯·巴塞特、亨利·德·康西尔、休·德·内维尔等。
第四集团,誓死忠于国王的人,都是国王的玩伴、弄臣,激起最大民愤的人,并且多数是外国人。包括后来在大宪章中明确规定驱逐出境永不叙用的那些人。
在场的教士都跟随着国王,其中大司法官彼得·德·罗切完全忠于约翰,教皇特使潘杜夫是约翰的老朋友,圣殿骑士团英格兰统领亚美迪克与约翰关系也不错,其他人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为首,保持中立,但在感情上同情反叛者。
因此,可能的情况是,星期一清晨,国王来到河边的草坪,第四集团的人都在国王身后警戒守卫城堡,陪同的是第三集团和教士们,而第一和第二集团则摆开阵势、引兵而来。这一天从清晨一直谈到日落,我们可以尝试作些想象,约翰会企图继续采用拖延战术,例如再次提出请教皇仲裁等等,而男爵们再也不吃这套,一定要当场签署文件才肯回营,最后约翰无奈,在“男爵条款”上盖了印玺。这份“男爵条款”应该是在4月27日由朗顿和马歇尔带给约翰的要求清单的基础上拟定的,在其间的一个半月,男爵们的要求应该处于不断膨胀中,因此这份文件更大的可能是男爵们当场提出,再由国王文秘署的书写员誊写,而不太可能就是4月27日的原稿。
之后的几天,双方继续协商具体的条文细节,最后形成63条的大宪章,交给文秘署细心制作完毕,再盖上国王的印玺。这些文本全部完成,恐怕要到6月19日,其间国王基本上每天都来与男爵们见面,看看工作进展情况。具体的谈判、文本确定工作,约翰较有可能不再参加,交给主教们或者马歇尔处理,我们在许多画作上看到的国王签字场面也未必确实,他是不是会写字尚有疑问,约翰可能只是加盖一个印玺,或者印玺都是由文秘署的官员加盖的。
6月19日星期五,应该是正式的签约仪式。首先,选出第61条规定的25人监督委员会成员,然后是正式的盖印仪式,授予文件正本,所有人宣誓遵守宪章,最后签发第一批交给各地郡长指示具体执行的令状。在这一天,国王和男爵达成了和解协议。
毫无疑问,国王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大宪章。为了确保条约的履行,宪章中规定了25人贵族委员会的至高权力,国王必须向各地郡长签发令状,收到指示者需要向25人
委员会宣誓效忠,确保宪章的完全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造反派:尤斯塔斯·德·维希、威廉·德·莫布雷、罗伯特·德·鲁斯、约翰·德·雷希、理
查德·德·珀西、克莱尔伯爵理查德、格罗切斯特伯爵杰弗里·德·曼德维尔、阿尔贝马尔伯爵威廉·德·福蒂布斯、温切斯特伯爵萨尔·德·昆西、海尔福德伯爵
亨利·德·伯亨、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格德、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小威廉·马歇尔、吉尔伯特·德·克莱尔、休·比格德、威廉·马莱、约翰·菲茨–罗伯特、罗杰·德·蒙贝松、理查德·德·蒙费奇、威廉·德·亨廷菲尔德、奥美尔伯爵威廉、威廉·阿尔比尼、杰弗里·德·赛伊以及伦敦市长威廉·德·哈德尔。
在这份名单中,实际上只有奥美尔伯爵威廉是始终忠于约翰的,最初属于王党的威廉·阿尔比
尼后来也起兵对抗国王,甚至成为叛军的军事领袖。因此,国王不可能感到高兴,甚或是一种达成和平的愉悦,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二十五个太上皇”。这个
男爵委员会也的确骄横跋扈,完全不把国王放在眼里,据说有一天男爵委员会去王廷裁判一个案件,国王恰好有病在身,无法起床,就请男爵们到国王的内廷宫室
去,男爵们居然大呼小叫地拒绝,叫人把国王抬出来摆到他们面前。
大宪章签署后,从现有的材料看,国王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他向各地的郡长发出令状命令履行大宪章,停止军事行动,停止征召他的雇佣兵。但是男爵们仍然非常担心,他们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在此之前,他们不愿意放弃伦敦,约翰只好同意男爵们继续占领伦敦,伦敦塔则交给大主教朗顿托管。按法律术语讲,这是一个合同的“先履行”问题,双方的义务总要有一方先履行,这个问题简单但却是无解的,如果双方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就无法继续履行。男爵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对方毕竟是国王,而且约翰的性格以暴戾任性著称。不过,如果本来就不相信国王会履行这个宪章,何必又要强逼国王低头,受此胯下之辱?如果本来就是要羞辱国王,一心谋反,那就应当尽快展开军事行动。男爵们在此表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妄想症状,一边想要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保自己的造反成果,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试探国王忍耐的底线,一步一步把国王逼到墙角。也许,男爵们有些兴奋过度,因为这个大宪章的条款,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从未有封臣可以逼迫自己的领主、强大的英格兰国王签署这样一个确认自由和权利的文件,他们在伦敦城里尽情狂欢,因为这里安全、富足,并且是权力的象征。
关于约翰,有人认为他签署大宪章本来就是缓兵之计,从来也没想过要履行,但是从证据来看,在文件签署后的几周内,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和诚信显然要超过造反的男爵。不过,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男爵们赖在伦敦不走,已经突破了国王的底线,任何人都需要安全感,当一个人感到了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必定会尽全力反抗,何况约翰毕竟是英格兰的国王,即使穷困潦倒,也是位强力君主。
约翰开始反击。一方面,作为政治策略,将大宪章送往罗马,呈送英格兰理论上的领主教皇英诺森,备述男爵们的造反举动,说明一大串道貌岸然的理由,比如男爵们的行为阻止了国王参加十字军东征,请求教皇撤销大宪章。另一方面,立即备战,国王召集他在法国的军队和弗兰德斯的雇佣军进入英格兰作战。
大主教朗顿和几位主教仍然多方奔走,希望避免内战,在7月16日安排一次新的会议。时间到了,国王并没有出席,却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教皇谕令,命令由温切斯特主教彼得、雷丁修道院院长和教皇代表潘杜夫组成三人委员会,有权对“所有针对国王和王国的动乱分子处以绝罚”。这项谕令表明,教皇已经对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把处罚权交给国王的朋友们。委员会要求大主教在教堂张贴教皇谕令,朗顿拒绝,于是委员会解除了大主教的职务,命其回罗马接受处理。
朗顿的去职导致再也没有人可以调停国王和男爵之间的关系,英格兰实际上已经站在内战的边缘。9月底,另一份教皇谕令到达,看来教皇被大宪章不慎恭敬的措辞激怒,完全听从了国王的说辞,谕令谴责了男爵们的阴谋反叛行径,并宣布大宪章完全、彻底、自始无效。随后的教皇谕令提醒男爵们,英格兰是教皇的封土,教皇是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判者。教皇在拉特兰公会上对反叛的男爵们处以绝罚。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男爵们在此表现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约翰的军队攻占罗切斯特城堡,俘虏叛军力邀而来的威廉·阿尔比尼,随后兵分两路,分别扫荡北方和南方,逐渐向伦敦紧逼,形成合围之势。男爵们仍然在伦敦城里毫无动作,他们唯一的对策,是联系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请求他派军队入侵英格兰,夺取王位。对于这个愚蠢的策略,实在已经不好再说什么。
约翰很辛苦,一边要对付男爵们的内乱,一边还要对付法国王太子路易的入侵。1216年10月19日,约翰国王因病在纽沃克城堡去世。这反倒成了形势的转折点,因为新君亨利三世年幼,约翰托孤于威廉·马歇尔,在他主持下立即重签了大宪章,釜底抽薪地消解了男爵和法国人的理论基础。英格兰才渐渐恢复平静,后来在1225年又再次重签大宪章,使之成为生效的法律。
对于大宪章本身的任务而言,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它无法维持国王和男爵们之间的和平,甚至无法维持他们之间的信任。作为法律文件,在三个月后它就遭到撤销,淹没在战争的混乱之中。就大宪章的内容而言,它的封建性质极为强烈,男爵们所要求的是他们的封建权利,理由是国王首先违反了封建契约,因此他们也就可以解除效忠的义务,直至国王再次承诺遵守。
需要注意的是,大宪章的谈判各方,完全没有现代的自由权利观——男爵们基本上是一群短视、自私的贵族,趁着昔日势力强大、精于压榨金钱的国王处于最最脆弱的时候,跳起来捞点好处;大主教从中调停,对于教会的权利寸步不让;伦敦市民按着商人的精明计算,做了一笔很好的投资,说实话,按当时的情况,押宝在男爵们身上的风险显然小得多。没有人关心国家的命运,甚至很少有人有国家的观念,因此当局势不利的时候,男爵们想出来的对策是请法国人来入侵,虽然路易进入伦敦城后宣誓遵守大宪章,但是我实在很怀疑法国人在大宪章的问题上会比约翰更讲诚信。
在所有卷入这一事件的人物中,威廉·马歇尔是最特别的一位。他是中世纪骑士的典范,武艺高强、忠心耿耿。在某些事情上,约翰对他并不很好,但是他从未想过反叛;他也知道约翰的性格不好,对于约翰许多暴戾的做法并不认同,沉重而蛮横的赋税甚至也直接伤害过他本人,所以他在内心并不完全反对男爵们提出的要求,在辅佐亨利三世后,他立即就促使新王重签了大宪章。也许,因为有这样一位处事稳重的忠臣,大宪章才没有沦为一些没头脑的男爵挟私报复的工具。
亨利二世所做的工作,是构建起一种有效率的中央政府机制,他重建了地方政府,推行中央司法和税收,试图克服封建主义的分裂和无效率。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他本人基本上是一名有节制的智者,尽管有时候仍然会爆发出家族遗传性的坏脾气,而当王位传递到他的两个儿子手里时,就开始发生麻烦:理查德一世是一名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骑士和艺术家,约翰则是个性格很不稳定的公子哥。因此,巨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君主?当中央权力强化之后,如何避免君主个人一时的好恶或者性格的突然爆发而导致的权力滥用?男爵们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们只是觉得国王压榨太狠,超出了封建习惯,因此他们按封建法律和习惯,要求恢复亨利二世之前的状态(亨利一世,甚至是忏悔者爱德华)。在此,一种追求效率的中央集权观念和一种追求限制的封建主义观念颇具神秘色彩地结合了起来,并且,感谢上帝,采取了法律的形式。这就是大宪章,他的生命力不在于当时,而在于之后的漫长岁月,甚至到了1965年,《英国制定法汇编》还承认大宪章中的9个条款为有效的法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某一时刻我们会迷惑于究竟是大宪章给了英国人自由,还是英国人自己的自由传统成就了大宪章的独特地位,无论如何,对于英国人而言,大宪章至今仍然是活生生的,是“法律下的自由”的象征。
兰尼米德的大宪章纪念碑是美国律师协会(ABA)出资修建的,现在每一年“大宪章协会”(Magna Carta Society)都要举行仪式纪念大宪章的签署,每一年,人们都要去看望那一片如茵的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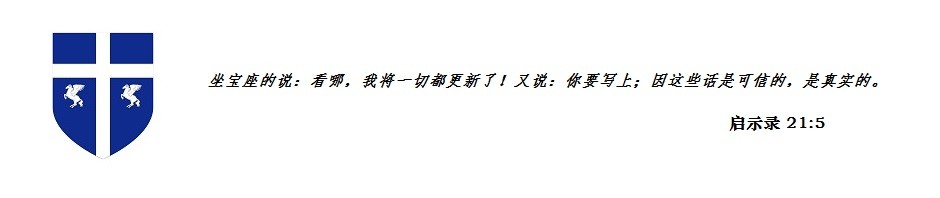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听说下次更新要等很久
俺百无聊赖只能挖挖坑排解无聊了
老徐啥时候来解释下错综复杂的教廷史和权力纷争
Freerain:很好看。因为有冲突就有故事性。加上场景、人物刻画一定会成为一部好书。当然这需要时间,写作很辛苦。我想你为“大宪章”而思如潮涌之时,定会披衣而起,秉烛疾书吧。看了第一篇,的确感到13世纪初叶的英格兰的确黑云压城、风云变幻。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我看来很“无厘头”的。中国历史上统一的目的很清晰。加上儒教的忠君思想。不似欧洲这些国家之间,明明同种同宗、通婚不断,却总是打了和,和了打。割土地象分火腿似的。教会太独立,既是矛盾的调解者又是矛盾的另一方。结果反而推波助澜。不过在财物保管上,教会是有作用的。战胜的一方把部分财物送进教堂。战败了则教堂难逃劫掠。我觉得这里你写到的外国、北方势力、教会和英王约翰没有原则区别。当然其中“法”的概念,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得到孕育。非常合理。我注意到:还有一种力量,就是英王希望由他们来保卫伦敦城的平民。他们似乎已经有些脱离贵族封建统治的自由选择权了。他们选择了正常的生活,连一般的警戒工作都没做。而争斗的双方都没有触及他们的生命财产。在文化比较上,我看到:中国封建文化的绝对和欧洲封建文化的妥协。而现在两种文化的表现正好相反。看约翰王传和陪着你思考,都是快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