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去日本,正好赶上前段时间的参议院改选,在网上聊起来眉飞色舞。选举的时候,整个社区的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投入,活力四射,大街上到处是候选人的广告,随处可见拉票的演说,有集会、有乐队;有一次听众中有个老头表示反对而当场跳起来与演讲者辩论,还有一次本地小县市的选举,有个候选人是个漂亮mm,在车站演讲拉票很是惹眼;有时候选举结果相当接近,大地方的选举之差几百票。兄弟很是高兴,因为感觉“天也是可以变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很高兴,连所在公司的小头目下班时还不忘提醒大家明天是投票日。
我想这就是政治所带来的活力吧。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放到我们的传统里遭到了很大的误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所说的“政治”(politics)是与“城邦”(polis)相连的,政治就是城邦的治理实践,而城邦的治理是民众共同参与的,因此“人”(城邦的市民)具有参与“政治”(城邦治理)的本性。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政治”通常与“权术”和“阴谋”之类联系在一起,天真或者虚伪一些的人说政治要以人为本、要讲道德,现实或者坦诚一些的人则直接说政治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就是赤裸裸的权谋,对于中国人而言,政治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长久以来,我们的“政治”与“胜负”联系在一起,变成一场竞赛,奖品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途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消灭其他竞争者。因此,当我们听到“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样的说法时,也倾向于叹服亚老的睿智,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政治”(权力争夺)实践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动物”(野蛮嗜血)的本性。
西方政治的活力,是民主参与,我们政治的活力,则是暴力斗争。所以,民主进入中国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我们不理解民主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不是玩权术,在这两个层面上,我们无法理解整体的民主政治机制。
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把城邦的管理任务交给一群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就像航行要请专业水手、看病要去挂牌诊所一样,政治也应当由“那个知道的人”负责。问题在于,贵族也未必就是专家,苏格拉底也承认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因此神谕才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的理论,柏拉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过他在叙拉古寻求哲学王即“那个知道的人”的努力遭到惨败,而波普把他作为开放社会敌人的源头也并不为过。不过,苏格拉底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雅典的民众大会直接裁决政务和案件的做法,也是有危险的,所以才有英国传统下的代议制政府,简单来说就是民众选举专家,如果发现专家不专,就再换掉。这种区别,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中小学教科书中的简单观点,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里都是有钱人(比方律师),而我们的代表大会里都是工人和农民。因为美国的工人和农民选举了这些律师,因为他们更像是专家,而我们的代表大会通过在各种职业中指定代表构成一个决策团体,只能在构成方面体现各阶层的参与。我们的大会时常面临雅典民众大会的困境,就是由鞋匠来审判苏格拉底,我们由工人公民决定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超级大水坝。
民主的面目并不永远慈祥,苏格拉底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苏格拉底杀身成仁,通过自己寻死凸显出民主制度的困境,他用自己的死嘲讽了民主。雅典的民众大会所犯的错误是,在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下,限制了言论自由。不错,苏格拉底一贯嘲笑民主、鼓吹独裁,并且他的学生中间有许多人亲自实践了僭主统治,但是并不能由于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将他处死。比方,对于我们稔熟的“也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如果你所说的,是要取消我说话的权利,我是否可以禁止你发表这样的言论、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你呢?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自由都需要得到保证。我必须承认,实际上所爱好的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也可能妨碍自由,历史上有几次“大革命”都是民主消灭自由的例子,因此民主也需要被监控。
话说回来,政治的根本目的何在?这是产生分歧的基础。有人认为政治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比如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或者,坦白一点说,政治就是追求权力所带来的快感,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政治过程中的民主,迟早也会变得面目模糊或者面目狰狞。哈耶克把宪政定义为“人的适宜状态”,所以在英美传统的理想下,政治的目的,也许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在1215年制定大宪章的所在地兰尼米德,后来修了一个纪念的小亭,上面所刻的口号是“纪念法律下的自由”。
民主的用途,第一是可以限制专断的权力,第二是可以使民众在最大程度上参与治理、鼓舞他们活力,这种自主的活力是国家和民族所必须的。埃斯库罗斯的剧本《波斯人》描写薛西斯入侵希腊,消息传回波斯首都,母后问信使:“谁是他们的牧人,统帅他们军队的主子?”,信使回答说:“他们(希腊人)不是谁的奴隶或臣民。”战争的结果是,有政治活力的希腊人击败了被鞭子赶上战场的波斯大军。兄弟看到日本的基层选举,觉得“开心”,就是因为这种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活力,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快乐。而在一个把权术当成政治活力的地方,民主自然会变得面目可憎,人们也不会因此产生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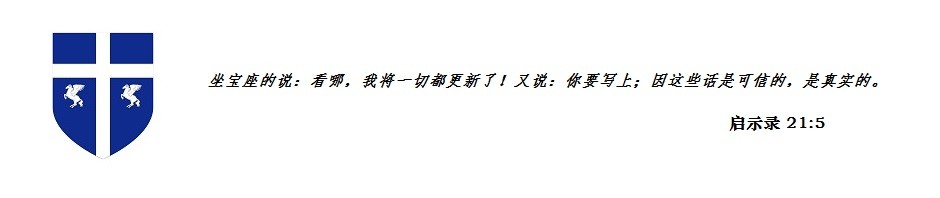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来自内心的快乐”,很贴切!
兄弟,侬老深奥额。
抢个沙发,明天上班打出来看比较合适.
除非真的做不掉对手,否则是很难提议要共存共事的。压倒性的优势让政客晚上睡得着觉。
研习过不少的生物学专著(而今全忘记了),感觉是,人其实不能跟人以外的动物相比–倒不是人太智慧这类的优势,倒是人比动物还要残酷的作态。草原上的狮子只猎杀够饱的羚羊角马。
任何游戏或游艺的中国化,都是要变态的。
工人农民和低劣的律师法务是一样坏,甚至更坏的不可救赎。
快感,真的是不错的追求,也和谐社会这样的政治目标更为实际和真实。
唐儒传承的日本,怀着阉割的民主,却也有几分可爱和希望。
“对于中国人而言,政治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西方政治的活力,是民主参与,我们政治的活力,则是暴力斗争。”但是在西方近代史上,不是也有血腥的政治权力斗争吗?就政治而言,西方与东方的政治斗争形式上可能不同,但是就本质而言,其残酷性与血腥,似乎并无根本的区别呀!
To Minjie:这里有部分语义学问题。西方历史中也有权力斗争,不过并没有认为这是“政治”的含义,他们从来没有什么“political power”的概念;我们则天然地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权力角逐。我读过一本牛津的政治学入门的小书,里面的定义认为不民主的不算是政治。因此,我们的困境在于,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没有民主和限权的资源可以利用。
是否可以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政治的定义被扩大化,包含了很多本不应当属于理想中的“政治”范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