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因为我在尚未了解沃格林的时候,就买全了他所有已经上市的书。他的书静静地站在书架上有几个月,我甚至没有仔细翻看其中任何一本的序言或译后记之类。直到这次春节放假,突然开始对诺斯替主义感兴趣,就开始读他的《没有约束的现代性》。没料到一读之下,大为兴奋,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阅读的时候在书上作如此多的标记,也很久没有在阅读中被引发出这样多的思考,也很久没有在阅读中体验到这样的愉悦感。正如他的一位学生和同事后来所评论的:“沃格林让那些心智开放的跟随者感到快乐。”
话题太多了,从哪里说起呢。
我想,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的诚实。时下的学界充斥着装B风气,所谓的学者们动不动就抛出些艰涩的词汇语句,里面却是一包稻草,高级一点的装B者,则动不动构建些什么理论体系,为了某个山头的头牌打得不可开交,甚至为此另立一个山头。沃格林大力批判近现代“构建体系”的哲学风潮,认为这根本违背了从古希腊开始的哲学的精神。哲学是“爱智慧”,这意味着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一个一旦建立永远适用的终极体系,他引用柏拉图解释:
苏格拉底描绘了真正的思想者的种种特征,费德罗问,人们应该怎样称呼这样的思想者,苏格拉底引用赫拉克利特说:sophos,知道者,这个词会太过分,只
能用于称呼神自己,也许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他为philosophos,爱知者。爱知者所爱的知,只能属于那知道的神,所以爱知者
philosophos,就成了theophilos,即爱神者。
他的批判非常有力,他认为黑格尔这样的体系建构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与实在经验相联系的“知识”(sophia),而是“灵知”(gnosis),是一种反哲学、反理性的巫术。而马克思虽然号称批判黑格尔,却在灵知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把观念的灵知推向现实的行动。而沃格林所厌恶的,是体系建构者们明明知道自己体系的不可靠和关键的硬伤,却仍然“为了建构体系而建构体系”,这就太过分了。所以沃格林把诺斯替主义称为“腐败的力量”。
其实,我认为自己长久以来所追求的,在根本上无非是诚实,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无论如何无法写出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我一直认为现存的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淘汰好人的体系,第一步就是入党申请书,因为,这份本人志向的声明一定不是出于内心的,淘汰好人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有不诚实倾向的人。而不诚实,确实是违背理性的,也是反哲学的。沃格林在“灵知社会主义”(作于20世纪30年代)最后说到:
一个已经达到工业生产层次的社会,其生存有赖于严格的科学理性的标准,禁止哲学会给这样一个社会带来什么,这只有在未来才能看清楚。……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作为信条予以贯彻的社会可能由于思想上的不诚实而导致负面结果。
沃格林强烈反对这种不诚实的伪哲学,是因为这种腐败的力量已经不仅局限在观念中,而是进入了实在而造成灾难。他本人在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掌权后被解除教职,惊险地在最后一刻逃离奥地利,所以他对此也有切身的体会。他分明看到了这时代的严重病症,论到尼采说:
谋杀上帝的人自己会成为上帝。……如果他想成为神,在自我偶像化的过程中,他将会成为一个魔鬼,蓄意地让自己与神断开。……人不能够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超人,试图创造超人就是试图谋杀人。历史地说,随着谋杀上帝之后产生的不是超人,而是谋杀人:在灵知理论家谋杀了神之后,接着就是革命实践者开始杀人。(《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
沃格林好像一个医生,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无秩序,并且这个病症已经极其严重,所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重建政治科学,实际上首先是重建哲学,回到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回归到那真正的、开放的、诚实的“爱智慧”中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重建秩序。他要求一种“知性的诚实”,而意识形态就是知性上不诚实的现象,所以必须与意识形态斗争。沃格林强调人“灵魂的敞开”,我们必须接受实在、理解它,而不是以一种反叛的态度试图用强力去改造它。人的经验性存在是位于人性和作为其根基的神性之间的一种“间际”(in-between)状态,因此人的经验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维持了人朝向神性根基的生存状态。人的异化,则意味着人的自我退缩状态,从生存的张力中退缩,就是从生存的理性中退缩,也就是从神面前退缩,离弃由人与神性根基的关系构建起来的生存。所以沃格林说“若不反叛理性,就无法反叛上帝;反之亦然。”(《自传性反思》)而那些人为建构的宏大体系,实际上是伪造实在,沃格林称为“次级实在”,意为不真实的、但由人造成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实在。所以,“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自传性反思》)
沃格林一直不受重视,因为西方的学界正陷于他所诊断的病症,而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尝试重建根基。他的博学和好学也令人咂舌,他懂得十几种语言,其中有许多是因为研究需要而专门去学习的,为了研究犹太教他向拉比学习希伯来语,为了研究中国他向同事学习中文,中文水平甚至达到从样板戏中辨识出周朝的歌词。他的研讨班门槛也很高,学生需要掌握一门古典语文(拉丁语或希腊语),能流利阅读德语、法语和英语,根据专业还需要懂得相应的语言。我觉得,沃格林尝试了一项现代人认为不可能的事,那就是恢复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家。长久以来,现代人对知识的领域分割再分割,似乎钻研得很深入,却丧失了站在高处检查挖掘方向是否正确的能力,沃格林正是要恢复这种能力。
或许,基督徒比较能够理解沃格林所说的“存在的张力”,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天天处在这种张力之中。
古典哲人的伟大发现就是,人不是“必朽者”,而是参与朝向不朽运动的参与者。不朽化——使人不朽的活动——作为哲学家的生存实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是核心经验。同样,保罗的伟大经验和洞见,乃是实在超越其当前的死亡结构向着不朽状态的运动(这种状态将通过上帝的恩典获得),亦即,向着永生或永存的状态运动。这种朝向超越当前结构的存在状态的运动,将一种更强的张力注入了生存秩序,这是因为,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指引生命,生命才会走向不朽的状态。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使自己的生活与这一运动相协调。相当一部分人还梦想着就在此世中抵达圆满的捷径。(《自传性反思》)
沃格林让我发现,此前我所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僭妄”,亦即人类进入近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上帝,存在理解上的不充分,这种不充分是因为站得不够高导致的。我毕竟也是现代性和后现代环境下的人,我天然地保持了一种线性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许多人认为没有终点,马克思说终点是共产主义,我们说终点是最后的审判。但沃格林对于诺斯替主义的批判提醒我,那并不是理性的僭妄,那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真正的僭妄罢了;另一方面,历史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诺斯替主义的幽灵在近现代复活,并正在不断侵蚀这个世界,经由它的现代继承人尼采、黑格尔、马克思,已经造成了许多重大的混乱。
回到中国,实际上,我发现孔子的思想比较接近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他有一种谦卑、小心翼翼的理性,不断地求问,从来没有想要构造什么体系。他留下的作品,在形式上和苏格拉底留下的非常相似,都是学生记载的言论和教导。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混乱、恢复秩序。沃格林回忆他的教学生涯,说德国(中欧)学生的优点在于知识丰富,有很好的古典教育基础,但缺点是浸淫在意识形态中,开放性不足,而美国的学生知识方面有缺乏,但不缺乏常识性思维,没有受意识形态毒害。而我们现在,大概是既严重缺乏知识,又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的毒害,在根本上还保持着一个反神的传统。
读沃格林确实是让人快乐的,那种找到知识的快乐,他的评论者说“沃格林之所以坚持不懈地探索,……或许可以说,是由原本意义的爱智慧所产生的感召力[而导致的]……”,他绝对没有体系建构者散发出来的那种令人不快的气息。沃格林也让我更清楚那种生存的张力,并坚定地继续寻求。他似乎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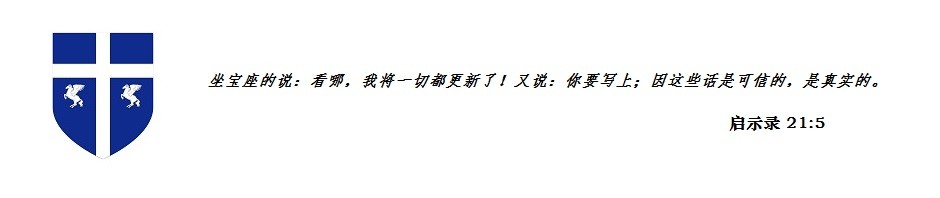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儒家也是很恐怖的,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Eric Voegelin?他对诺斯底的批判可以看看,不过,其他的,也要谨慎!
读你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但是,读一位非基督徒的作品,当他言及神,因为他没有圣灵,我们是否应该更加谨慎?尽管神已经显明在每个人的心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我不知道沃格林是否是基督徒,我无法确实地断定他有没有圣灵在里面,只是从他的一些观点来看,我觉得他有可能不是,或者,至少不是严谨的加尔文主义者(他已经被贴了无数的标签,其中也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但是他的一些洞见非常有启发意义。其次,他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并非由于对神性、救恩一类主题的阐述,我觉得他的论述是哲学性的,是在“真正的理性”方面,理性同样是神所赐的,我们有理由开动我们的理性去探究,哲学并不是信仰的敌人。沃格林的观点是,理性本身就是与顺服神相联结的,而他关于诺斯替主义的分析,对于深刻理解这个世界当下的状况非常有帮助。我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发现,他的分析对于帮助改进护教学应用方式很有促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相当认同他。他也促使我反思,我们的信仰中,是否存在腐败的意识形态成分。
腐败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不诚实的敬拜吗?
范泰尔护教学的关键在于前提,不信者的前提是靠不住、经不起提问的,而那些体系构建者一旦遇到对其前提的质疑,就会采取不允许提问的命令。沃格林说他每每与黑格尔主义者辩论到一个地步,触及前提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就会变成“你要么成为黑格尔主义者,要么就闭口”——我觉得,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腐败性,那是很不诚实的。
我一直认为我们信仰的前提恰恰是非常实证的,因为是真实的,所以应该相信。当我们遇到对这个事实的质疑,我们到某个阶段会停止辩论的原因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在终极问题上寻获百分之百的证据是无能的。这种基于事实的信仰和某种基于观念的意识形态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吧?
你说的没有错。所以我们的前提是与不信者的前提完全不同的,护教的时候,需要指出这一点。我们停止追问与体系建构者不允许提问是完全不同的。沃格林让我看到的一点是,问题并非是理性无能,而是真正的理性必定指向神。意识形态的不诚实在于,明明知道自己的前提出现了内在矛盾,却仍然“为体系而体系”,硬撑着不许别人提问,这就腐蚀了理性。实际上,如果保持理性,就不会有这种建构体系的企图,理性不尝试解决终极问题,因此构建终极体系的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是反哲学的,也是反神的。这个问题马上涉及到诺斯替主义了。我觉得基督徒的意识形态症可能表现为对某种神学体系(或者灵性体验)的偏好,这个需要警惕,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影响个人的救恩,但很有可能阻碍神的工作,这是需要反省的地方。
另外,关于“实证”。实证主义恰恰是近现代意识形态的源流之一,实证主义否认除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以外存在其他的科学方法,这就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事实上,但是这个事实形成的路径,与实证主义者所持的路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追究前提的原因。
你的提醒非常有益,我们的前提不是假设,以便构建体系,我们的前提是事实,只有事实。那么神学如何理解呢?建构性的神学难道都是一种狂妄吗?
所以,神学首先必须忠实于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不存在“建构性的神学”,因为一旦开始建构,就很容易走向不信,这也就是所谓新派神学的毛病了。
但如何又能保证现行圣经的准确无误?须知詹姆斯王版本并非圣经的唯一版本。而且又如何保证圣经在不同语言传译过程中内容的正确性与唯一性?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神学首先必须忠实于圣经”岂不成了无本之木?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是神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救赎计划。确切的说,钦定本并非圣经的“版本”,而是“译本”之一。我确信原本圣经的准确无误,在传译过程中会发生不确,这就需要我们考察研究经文(我发觉迟早要学习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幸而我们有很多非常可靠的原始抄本,死海古卷这样的历史发现更加坚定了圣经的可靠性。我空间的资料区“信条”部分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可作参考。
你看了那么多书,写一点读书笔记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