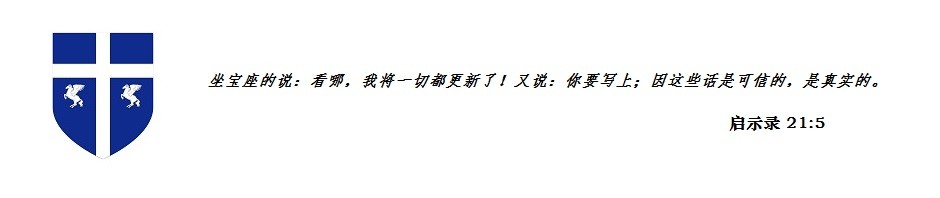春节闲来读书,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是没有“史诗”的。
这是个挺有趣的问题。许多民族都有史诗,从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到荷马,又到中世纪西欧的武功歌,出现了很多歌颂英雄事迹的史诗,藏族还有一部巨长的《格萨尔王传》,据说到现在还可以唱。但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人众多的地方,却没有出现类似的作品。
史诗是种很有趣的现象,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往往有历史事实做背景。近代的希腊史家们纷纷把《伊利亚特》当作虚构的传说,但是格罗特的希腊史巨著尚未印行几版,业余考古家谢里曼居然就凭着荷马的作品按图索骥把古城挖了出来,由此人们才发现,古老的史诗原来是“真”的。还是《指环王》开场的旁白说得好——“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
史诗有两方面:历史和诗歌,而这两方面又指向历史和诗歌的作者。
历史和诗歌都是值得人尊敬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持有历史和诗歌的人都被尊为智者。荷马是个游吟诗人,这个职业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或者没有继承关系,是各地自发的)。在这个传统下产生了史诗,史诗是历史,也是诗歌;它叙述历史事件、表达历史思绪,也给人带来文学和音乐的美感,让人传唱。
后来,开始有了史家。这一些史家一个人身份记述历史、作出评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都是个人,哪怕是统治者自行作史,比如凯撒的《高卢战记》,也是以个人的身份,接受众人的评价,以政令的方式编写一部历史,是相当可笑的。另一方面,在诗歌,诗人们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维吉尔作《埃涅阿斯记》,是把自己当做诗人,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当然,奥古斯都也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他的作品还是流传了下来。
史诗需要一个有空间的、活泼的、有鉴赏力和创造力的民间。《罗兰之歌》问世的时代,史笔掌握在修士手中,在一个搞不太清楚时间和纪年的时代,他们在修道院里辛勤地编纂那些编年史。《罗兰之歌》在史实上有偏差,把巴斯克袭击者改成了异教徒,把查理曼的反击夸大了许多倍,但是,直到今日这首歌读来仍然能激起人心中的热血。《罗兰之歌》、《熙德之歌》这样的作品,通过游吟诗人在欧洲各地传唱,可以在乡间,可以在宫廷。国王们尊重诗人,这种关系本身甚至都成为一种史诗,比如狮心王理查被俘、下落不明,他的诗人布朗戴尔背着琴去欧洲大陆各地传唱,终于在迪恩施泰因城堡的高墙下找到了国王的应和。
中国的情况则相当不同。
顾准先生引范文澜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史官文化”。中国的历史,都是官史,也就是说,历史的作者是官方,我们所说的“正史”,不是说这史书更正确、更正义,而是说它的“名分”更“正统”,它受到统治政权的认可。个人修史,通常称“野史”。野者,非在朝堂。另一方面,我们的文人,基本上也要接受政权的认证,诗歌,可以作为进入公务员序列、进入政界的踏脚石。文人对自己价值的认可,也不完全在文学本身,如李白这般的文才,还是觉得自己受屈了一辈子,因为不得做官,个人抱负无法实现。
这两个传统,源头似乎在孔老夫子那里。孔先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编定《春秋》,另一件是编定《诗经》。《春秋》,原本是鲁国的编年史,经孔夫子编辑后,据说是微言大义,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统统写在里面了,于是这部史书就成为“经”,用于载“道”,我们现在有时会提到“官方意识形态”。而《诗》,原本是很多的民歌,孔夫子把自己认为不合适的加以删减,余下的就是“健康向上”的作品,大概可以起到“鼓舞人”的作用。来自民间的材料,经圣人改定,就成为官方认可的作品,避免诲淫诲盗,带坏小孩子。所以,中国的历史和诗文,基本上握在官方认可的作者手中,民间的作者和作品,如果不进入官方领域,很难保持自在如意的状态。
但是民间总有民间的声音,尽管失去了知识分子,这种声音仍然会以某种形式传达出来。而官方对这种声音往往相当警惕,管它叫“民谣”。“谣”的意思,大致是“不靠谱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所以中国人管谎话叫“谣言”,管诽谤叫“造谣”,管不着边际的消息叫“谣传”。到王朝末期的时候,皇帝通常会比较留心民谣,因为据说民谣预示着王朝命运的转变。至于对付民谣的方法,就像对付农民起义,一曰剿,一曰抚,一边是压制,一边是招安。在这种双重策略下,民歌尚且受到严密控制,史诗就更不可能诞生了。
多年不看春晚。今年只看一眼节目单,有三个“草根”歌,现在好像是红了,属于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不过,大约无非是在略有些馊气的燕鲍翅中间摆上一盘韭菜,根割得很干净,撒上点水珠。所以,我猜西单女孩不会再回西单街头,两位农民工歌手也不会再在地下室光着膀子唱“春天里”——都上春晚了啊,你还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