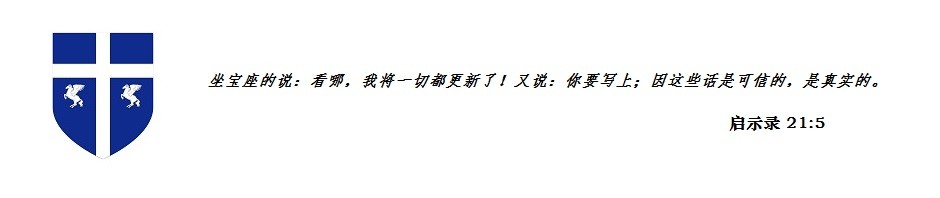我对历史感兴趣。因为当我们面对重大的决定是,时常需要追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走到今日这般境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历史研究。这世界,是个意识形态的世界,有时表面看来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实际上却共享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而历史研究,是意识形态的解毒剂。
说了一段废话作为开头。我关心的问题是:今日的中国基督徒,要如何处理关于地上的权利的问题,这个权利,是指政治和人权权利。我们身处在一个民族国家,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极权的国家,我们需要怎样去面对这一切?
诚然,圣经是基督徒生活准则的基石,但可怜的人们还是陷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中。圣经说,天国不属这世界、我们是寄居的,圣经又说,要尽管理这地的责任,要尽本分;圣经说,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要安于这身份,圣经又说,真理必叫你们自由;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即便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圣经又说,当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圣经说,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圣经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尤其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增多,教会规模日益扩大,开始与世俗的政权有了不和,该怎么办?我为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们切切地祷告,也觉得必须尽可能理解和说明问题,否则就都算不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关于这个问题,起初读到的是王怡长老翻译的《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读过之后,觉得不尽兴,很多问题似乎点到了,却又没有说得很明白。我们不能把现代的自由宪政政体简单地归结为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的理性和解放一样。加尔文毕竟同意烧死塞尔维特,那么他的理论最后又怎么引向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和美国的政体和理论呢?然后又有一本《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在我看来其论证更为粗糙,几乎是反向的《货币战争》。
今年,终于等到了《权利的变革——早期加尔文教中的法律、宗教和人权》。一直无暇研究,这几天觉得问题在脑子里打转实在等不下去,只好放弃写一篇正规的论文的打算,读一点,写一点,发一点感想了。
本书作者约翰·维特,伯尔曼教授的弟子。伯尔曼教授以《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等著名,他在前书中认为希尔德布兰改革之后的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具现代国家形态的组织,对中世纪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解析。维特教授的专业方向似乎在法律与宗教的交叉研究。
我初读本书后,觉得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尽管作者是法律和宗教交叉研究的专家,对基督教新教的基本教义和理论的把握超过国内的同类型学者,但他很可能并不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尤其并非一位对改革宗(加尔文宗)教义和理论有深刻理解的基督徒。因此,需要注意本书封底推荐分类为“法理学”,而其中的观点,对国内的法律学者而言可能觉得“开拓了眼界”(居然可以深刻地引向宗教),但在一个基督徒看来,许多方向却并非正解。而本书所研究的问题,与我关心的也不尽相同,本书关心的是,现代欧美国家的法律、人权和宪政制度,可以如何追溯到加尔文主义,其中的源流变化如何。
在导论中,作者承认,他是在众多的研究对象中选择了一些特定的代表人物提出讨论。那么,他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实际上是从一位法律学者的视角出发,他所说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位法律学者所理解的加尔文主义,尽管相比其他许多学者,他对加尔文宗的理论已经可算是相当熟悉了。事实上,在我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种隐隐的偏离改革宗的路线。因为,对头两位人物,加尔文和伯撒,基本上不会有争议,他们的塑像至今还一起站在日内瓦供改革宗分子瞻仰。但是此后的两位,荷兰的阿图修斯和英格兰的约翰·米尔顿,则已经开始偏离神学家-牧者的序列,进入法学家-政论家的系谱,米尔顿的一些言论,看起来已经完全偏离改革宗,甚至完全偏离基督教的教导(《魔鬼代言人》里,魔鬼就取了他的名字)。
作者也同样说明,他的观点是:现代的人权、宪政制度不像长久以来的共识那样,单单是从启蒙运动一系源流发展而来,而是同时具有基督教新教的渊源,尤其是改革宗。这个观点,是很可以讨论的。实际上,我倒是同意作者这个观点,但是对此的解读不同。从现代的人权、宪政制度确实可以辨识出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两条源流,但是我认为这两条源流并不是一种合力,其中也存在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从本书作者对研究人物的选择就可以刊出,越是走向现代的制度,作者的注意力就越偏向世俗。
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按薛华博士的观点,是从同一个山顶融雪而成的两条方向相反的河流。启蒙运动高举人的主权,宗教改革则高举神的主权。这两股源流,在一开始相互之间的距离还不算太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二者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这也恰恰是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上面提到本书作者在提取代表人物过程中的倾向,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点。此前的学者,认为启蒙运动造就了权利学说和制度,维特教授则提出其中也有宗教改革的贡献,并作了梳理。实际上,从他的老师伯尔曼对教皇革命的研究开始,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旨趣。
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股源流有很大的差别,尽管表面上看来相似。作者在导论中说:“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将权利奠基于自然法和古老的宪章,新教改革者将它们奠基于圣经文本和神学人类学,欧洲和北美的启蒙运动作家将权利奠基于人性和社会契约。”——虽然承认新教对自由宪政的贡献,但我认为,将之并行于启蒙运动,是不可靠的,也混淆了改革宗的基本立论。
当然,本书确实是一种法理学的研究,在导论中,概述全书内容后,维特教授转向“迈向一种新的欧洲权利历史”的论题。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就是权利的历史变化,他并不关心基督徒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这一点我们完全不能提出责难。只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可以把这本著作作为很好的基础材料,来进一步澄清问题和提出自己的想法。
另外,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觉得对于所思考的问题不是不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整体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对处于社会中的教会和基督徒所面临的真实的处境有所了解。
第一章自然是从日内瓦和加尔文开始,题为“加尔文神学中的适度(宗教)自由:最初的日内瓦试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