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的长子暗嫩恋慕他的同父异母妹妹他玛,听取奸人诡计,设圈套强奸了他玛。但是,当他成功之后,却马上变脸,把他玛赶了出去,这个怎么回事呢。
本章开头说“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在这一节中,我们看见圣经强烈提示暗嫩和他玛的兄妹关系,其次,又强烈提示我们,暗嫩所爱的是他玛的美貌。暗嫩不择手段地占有了自己的妹妹,当他的肉欲得到满足,就突然开始产生一种厌恶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国传统也有所谓“始乱终弃”,才子佳人的故事,有三种结局,一种是喜剧、终成眷属,一种是悲剧、要出人命,最后一种大约是正剧,就是始乱终弃了。实际上这种结局相当多见,而传统的态度并不认为是男人的错,如果士子对妓女始乱终弃,通常被认为是“回到正道”。心理学上的评论是,对于这种不当的行为,人的内心深处都会产生羞耻感,而逃避的方法是将这种羞耻感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这是一种在身体暴力之后的精神暴力。
我们知道,神是严禁乱伦的,也禁止乱伦的婚姻(见利未记)。不过,他玛在遭到强奸威胁时候,这样说:“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我认为这是他玛情急之下的脱险尝试,希望暗嫩可以停下来,寻找正当婚姻的可能性,虽然兄妹之间的婚姻是被禁止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比如亚伯拉罕)。当然,大卫实在不太可能同意此项婚姻,而暗嫩一心想要的,也只是肉欲的满足,否则一开始就应当尝试一下向大卫提出婚姻的要求。所以他玛在此并没有什么罪过。
而他玛所说的其他话语,可能促进了暗嫩自己的羞耻感:“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作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这个羞耻感比一般人犯罪的羞耻感更大,涉及到神选民的身份,所以暗嫩事后的心理波动也显得更大。他把他玛赶出去,对仆人这样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闩。”非常粗鲁,非常无情,非常野蛮。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人心里放了一些东西,人们无法逃避,但不敬神的人,通常会以更大的罪来掩盖之前所犯的罪,而不是以悔改的心认罪。所以暗嫩“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更甚”,因为他必须让这种仇恨超过之前的亲近,否则不足以暂时遏制自己的羞耻感。这种方法当然是饮鸩止渴,使人沉迷于犯罪,越陷越深。根本的原因,在于不信神。先知以西结论到以色列人背离神时,将他们的行为比作淫乱,并且说:
[以西结23:17] 巴比伦人就来登她爱情的床,与她行淫玷污她。她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
人从犯罪的心出发,不可能寻求正确的关系;人在犯罪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
暗嫩的罪在此就显明了,后来他得的报应也是由此而来,被他玛的哥哥押沙龙所杀。另外,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卫的处理也有问题,虽然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愤怒,但是显然没有对暗嫩做什么惩罚(按律法是死罪),最后押沙龙的反叛也可能在这里埋下了一点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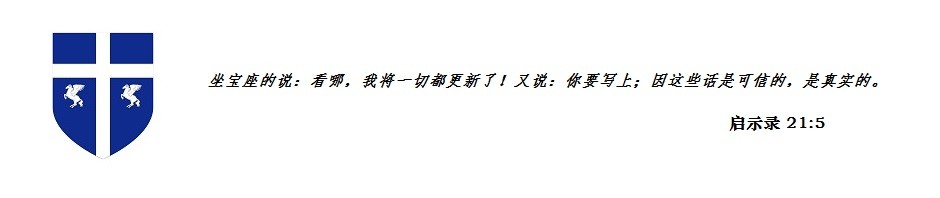
申命記22章28-29節:如果有人遇見一個少女,原是處女,還沒有許配過人,就抓住她,和她同寢,又被人發現,那和她同寢的人就要把五百七十克銀子給那少女的父親,那少女要歸作他的妻子,因為他玷污了她;他終生不能休她。是的,很多律法,以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完全無法理解,那我們該怎麼辦?
利未记20:17 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亚伯拉罕处于族长时代,其时,摩西律法尚未颁布,因此,以利未记的角度衡量亚伯拉罕并不合宜。同时,暗嫩他玛事件也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其主旨不在于教导正确的爱情,与其后一系列事件相关之余,更与神对大卫之约相关。
1、举亚伯拉罕的例子,并非要以利未记中的律法评价亚伯拉罕的婚姻,而是为了说明他玛在情急之下的脱险计策有某种依据(老鹰的引用可为另一例证,创世记中示剑强奸雅各的女儿后求婚也可为例证)。2、此处论及暗嫩他玛事件也并非要教导爱情观,所论的只是极小的一点,就是暗嫩为什么在犯罪以后突然恨恶他玛。3、看来还是有必要说明本篇的由来,这是夫人写“管锥编”读书笔记,论及人类情感的“相反相成”等等而引出的。兹录夫人手札如下:情感的三分与相反相成 钱先生说“‘哀而不伤’,哀且复判别差等”,又说“分而不隔,不特心情为尔”。伤是深度的哀,隔是彻底的分,这种表达正是庞朴先生在《论一分为三》中提出的三分法的四种思维形态之第二种:A而不A’,如威而不猛、乐而不淫等,是防A的过度。哀是一端,伤是另一端,哀而不伤就是中间的模糊地带,如黑与白之间还有灰的过渡一样。看到这一点是好的,但若像《唐诗品彚》提要那样从“寒温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引申出“四时无别”的结论,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到“边围含混”,未看到“核心明确”,犯了执中为一的错误了。 钱先生分析情感的“反亦相成”,举“冤家”一词为例,说《烟花记》中对“冤家”的六种解释只有第五种是憎,另外五种都是爱,乃是故意说反话,如同打情骂俏一样。但笔者以为爱极与恨极都是走极端,均会伤及中和之性,是伤身的事情。那五种情况虽是爱,但并非甜蜜厮守,而是生离死别,以致“寝食俱废”、“悲泣良苦”、“抱恨成疾”,如此痛苦,能不谓之“冤家”乎?所以若从带来伤害这个角度来看,“冤家”一词包含的爱憎矛盾是否可以消解了呢? 钱先生复举谭嗣同《仁学》中的杀和淫“其情相反,其事相因”为例,说淫即爱,杀即憎,又是爱憎难分。但笔者以为不可将淫与爱划上等号,淫纯属肉体的欲望,爱则是灵肉的合一,而且更强调灵里的满足。关于由淫转憎,《圣经》里暗嫩和她玛的故事可说是绝佳的案例。《撒母耳记下》13章讲大卫王的儿子暗嫩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她玛,装病叫她玛来照顾他,趁机将她玛强奸了。经上说:“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他把她玛赶了出去,没有负应负的责任。钱先生只注意到了“其情相反”,但这里的情也并不是真爱,只是一种冲动,无论是淫的冲动还是憎的冲动。而且他没有注意到“其理相一”,在杀和淫之间其实贯穿了同一个理,即都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淫欲、发怒都是一种血气之欲),追求满足自己。暗嫩赶他玛出去时,他玛说:“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可见这样的淫与杀、“爱”与憎都是犯罪,在谭嗣同看来都是不仁了。关于暗嫩为何会恨她玛,有人说是得到的痛苦,因为美幻灭了(1926年向培良剧本《暗嫩》),笔者猜测是他犯罪以后心理压力很大,就在自己的心理暗示中把责任推到了她玛那里,怪责她玛引诱他犯罪,所以恨她玛。由此也可见出人类情感之复杂善变,是谓“反亦情之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