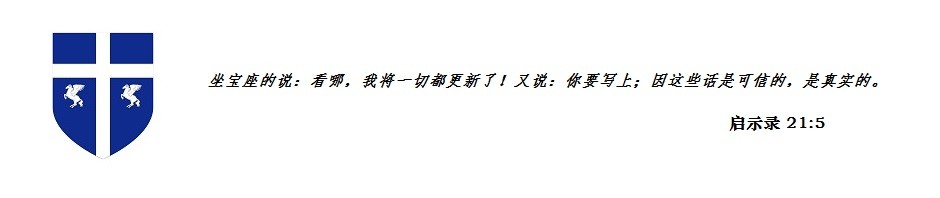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许多争议,公教授的观点是:目前共产党未进行改革的原因是政治理论准备不足。这个观点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嘲笑。我觉得嘲笑和反讽是没有建设性的,我们当下的一个危险就是在公共领域形成一种反讽文化,任何重大和深刻的问题一进入公共领域就丧失讨论的环境,沦为民众嘲笑的对象(当然,这个问题和官方长期的压制言论有关,此处暂不讨论)。
我不愿意先推测持论者的动机,我觉得公教授提出的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计划中的博士论文将研究亨利八世在推进宗教改革(英国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更是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结构重造,故谓Reformation)过程中,官方所主导的理论建构活动。就我的学术关心而言,始终是在当下的中国。中国自清末以来,所走的是一条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从效率低下的传统国家艰难地向高效的现代国家转型。就目前而言,国家榨取资源的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但仍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原因在于尚未建立一种限制权力的宪政机制。一种限权机制对于国家建设极为重要,使国家榨取资源的能力得以持续发展,而不至于在内部的矛盾和不满中解体。直白一点说,就是如何在取得民众同意的情况下,让他们拿出钱来建设国家。对此我更多考虑欧洲而非美国,因为美国的情况太过特殊,那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实验的产物,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再有一片“新大陆”让一群人商谈如何建立政府。我们必须在一个存在长期传统的环境下进行改革。我说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革命。每一次真正成功的革命,都以外在的改革为形式,以此强调和确认其历史延续性,而每一次高呼“时间开始了”的革命,往往无法在实际中改变传统。
我之所以要研究亨利八世的改革,是因为这是一次国家结构的重大转型,而这次极其重大的转型,竟然只因其如此小的反叛和抵制,就得以完成,一定有理由。亨利八世的改革,从一个权益的个案(离婚)开始,逐渐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可以辨识出三个步骤,首先是理论建构(理论准备)。理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建构,亦即拍脑袋。但这种理论建构活动要能够说服人才行,而首先必须说服自己。共产党为何能取得政权,因为在当时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被共产党人自己和许多民众热烈相信的理论。而我们现在确实极度缺乏一种理论。有人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反驳公方彬,我认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我们不能一直赖在邓小平那里,邓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理论,现在缺乏一种被多数人相信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转型的瓶颈。我们必须要进步,而不是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一切都正确。
改革的理论建构完成后,下一步也极为关键,就是立法。在这一点上我们遭到了传统资源贫乏的困难。欧洲具有强烈的法律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中世纪的教会。(实际上,亨利八世的改革可以与中世纪的另一次重大改革相比较,就是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在教皇革命中,格里高利七世的措施与亨利八世的改革有极强的相似性。)亨利八世在建构起一套王权理论后,就迅速将其付诸于立法,通过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将理论现实化。同时,亨利也利用了英国长期以来的议会传统,这一点对后来的发展也极其重要。亨利八世正是通过《限制上诉法》、《王权至尊法》等一系列制定法,为他的智囊团所建构的理论预备好进入实践的条件。在欧洲传统下,一种国家构建的政治活动最终采取了法律的形式,乃是因为法律的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好像钢筋骨架,能够支撑起社会的重大改变;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能够通过司法进入现实和影响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不反对“法律工具论”,只是时下的统治者对法律的工具意义理解太差,把它当作纯粹压制的暴力工具,这简直是杀鸡用屠龙刀,法律的工具意义可以扩展到国家建设层面,带来极大的好处,建立秩序和信仰,也使统治得以长久稳定。
另外,对于建构起来的理论,亨利八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以造成一种民众的意识形态。在今日,民众与历史上的所有时期相比并不更加智慧,因而同样是可以影响的。比如,民主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如今的时代,民主已经是一种共识。改革必须争取大多数人的同意,否则一定无法进行,对于上层的改革设计者而言,用一种可信的理论影响民众争取支持是必须的。
最后,制定好的法律还必须经由司法过程进入实践。亨利八世是这样做的,用不大的代价压制一些反对者,促使局面稳定。这一步骤实际上是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展开。接着,还可以逐步采取其他政治行动(在亨利八世那里是解散修道院)。
所以,在一种存在长期形成的传统的环境中,要进行成功的革命性的改革,必须要有理论准备。并且,这种理论准备必须有历史连续性,哪怕是“建构”出来的连续性,只要多数人相信就行。这也就是我在上一篇中说的“旧瓶装新酒”,革命最终的成功,一定是在酒瓶中慢慢灌上新酒。
在这一点上,公方彬提出“进行理论准备”、“形成新政治观”这些说法并非仅仅官方宣传。但问题在于,公的观点抛出遭到如此众多的反讽,表示我们可用的资源仍然极度缺乏,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共识太少,要完成改革的第一步“理论准备”非常困难。我觉得公的身份和理论嫌直白,至少从现实结果来看没有形成有效的说服力。因此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建构,理论建构的领域,应当首先在法学、史学和政治哲学。比较可惜的是过去十年法律、司法体系和法学建设前进不力,大有倒退之势,令人担忧。
总之,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必须有理论准备,然后才可能有立法和实践活动。不过,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顶层是否有诚意,如果没有这一条,一切都白给了。
最后我要说的是,地上的国是暂时的,其实也不必太过在意,只是人在此世,总要尽自己的本分,我若是名学者,自然尽力就自己的学术关心工作,凡事之成就都在上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