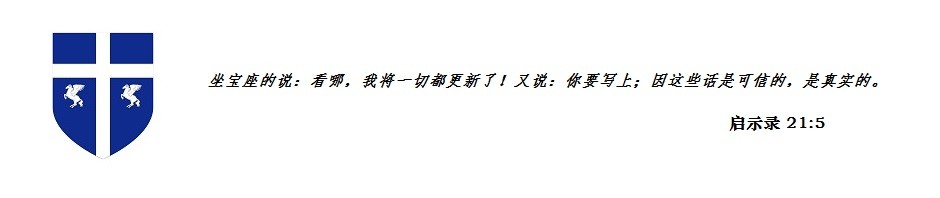在绪论的起首,施罗默·桑德教授讲述了三个故事。故事中的角色包括波兰裔的犹太共产主义者,他始终怀念东欧的犹太社会;娶了犹太妻子的西班牙自由战士,他的民族和宗教信仰都被记载为“加泰罗尼亚”;流落在以色列的阿拉伯诗人,在这片土地上吟诵着他者之歌;金发的俄罗斯裔犹太学生,被视为异类。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在面对以色列这个犹太民族国家时,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冲突、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焦虑感;另一个共同点,则是与桑德教授有个人的联系。
或许并不是每一名以色列人都像桑德教授那样对犹太民族和国家问题有如此深切的切身体验,但这个问题显然激发起了许多人的关心,甚至是在遥远的中国。我们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代,在这个世界中,国家的形态基本上只有一种,那就是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规定了作为我们生存前提的世界生态。当我们面对因这个大环境而来的焦虑感时,就不由得想要追溯其来源。
现代国家起源于西欧,西欧的现代国家起源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打倒了天主教会,其中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启动了一个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在于粉碎了普世主义,自威斯特伐里亚之后“谁的土地,谁的宗教”。也就是说,宗教在两方面被同时降格,一方面须服从于理性,一方面须服从于国家。而历史,按桑德教授的意见,则成为“宗教信仰合适的替代物”,甚至本身就成为一种(世俗)宗教。
民族和国家历史成为世俗宗教,是由于历史和史学本身的一些独特性质而造成。首先,历史具有天然的神秘性,因为人们无法测透历史,因为它诉诸于“超越人的记忆”的过去。宗教改革之际,亨利八世正是将与罗马决裂的理由建立在历史论证之上,“英格兰自古以来就是帝国”,基于本民族那源远流长的历史主张排除外来势力(教宗)的主权权利。其次,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具有某种“科学性”,通过历史学家的技艺,历史叙事逐渐脱离了文学形式,转变为一种十分据说强调证据和客观性的论证形式。由此,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就成为为其主权加冕的大祭司,各国概莫能外。建立一个国家,就需要构建一套历史叙事;消灭一个国家,也需要涂抹该国的历史。
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相当晚近的事,在1947年的联合国决议前,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甚至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前身。这种状况决定了以色列及其国家建设进程的特殊性。以色列必须以近乎无中生有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国家历史叙事,但犹太民族的历史实际对这项工作构成了很大的困难。
以色列国家遭遇的第一个矛盾,在于必须以圣经作为构建历史叙事的基础。犹太人没有从都铎王朝到现代英国的历史,也没有从康乾的大清到现代中国的历史,他们必须填补这个空白,向上追溯,直到罗马帝国时代的犹太国家。同时,犹太人也不是有史学传统的民族,它没有喜好考察研究的希罗多德,没有勤勉的修士编年史家,也没有试图以史承载“大义”的圣人。犹太人所拥有的是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的一神论宗教,他们的典籍是圣经,圣经的目的是神学,而非历史;他们自我保存的方式也不是政治国家,而是宗教。
旧约包含一种独特的神学,据此,犹太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与其他民族严格区别。在这种神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现代民族身份反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将古老的神学用于建立现代国家,本身与世俗化和理性化进程相悖。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叙事的世俗宗教,也就存在诸多矛盾因素。所以,犹太学者们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调和圣经的神学性叙事、使之符合现代史学观念。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动用极大的勇气填补甚或掩盖某些裂缝,于是这座史学大楼就带上了许多野蛮施工的痕迹。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形态从欧洲发展到美洲,在不断的竞争中追求效率和稳定的平衡,国家机器一方面提高效率从事战争和战争准备活动,另一方面则必须兼顾整体的稳定。由此形成了起源于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平等和民主的政体。因为一旦将主权的来源从上帝手中夺去、交给民族历史,那么国家迟早会走向某种形式的人民主权,而人民的平等和民主在逻辑上最能与人民主权协调一致。平等和民主将成为现代国家的另一种世俗宗教,形成某种世俗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以此缓解传统宗教普世性解体后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普世性的理念具有更大的力量,能够促使人形成信仰、为之牺牲。在具有极大力量的意识形态叙事之下,国家将获得最大的安全、秩序、效率和动员能力。所以桑德教授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就直指“民主就是民族主义的内核”。
犹太人并非没有考虑过平等和民主的叙事。当现代国家进程启动发展之后,犹太人仍然散居在各国中。因此,最初的计划并不是如复国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召聚各国中的遗民、回到传说中的祖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单一民族国家。最初的计划大致是融入自己已经所在的民族国家(从斯宾诺莎起大约就是这一路线的计划)。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尽管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出于各种原因(宗教的,或是经济的)对犹太人保持长期的敌视,但现代国家出现后,其平等和民主的主张使得犹太人有可能融入所在国。犹太人可以首先成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其次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
这样一种计划在德国遭到失败,多少是因为德国人有自己的国家建设和历史叙事问题。奥斯维辛使犹太人不再考虑最初的计划,尽管这样的安排在许多地方(比如美国)已经颇为成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下定决心不再依靠别人给的平等和民主,他们要离开万国,返回耶路撒冷,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处置纳粹分子艾希曼。
以色列国家遭遇的第二个矛盾,在于必须以单一民族的纯粹性作为构建国家叙事的基础。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建设过程起于民族、终于国家,单一的民族历史叙事最终归结为另一个追求和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叙事,民族叙事将破坏宗教普世性,民主叙事则将重塑世俗宗教的普世性。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是第一的,民族是第二的,这样,就能够在国家之下容纳不同的民族,消解单一民族叙事本身天然的不足及其对国家合法性造成的负面作用。但以色列国家无法采取这种方式,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本就是由于平等和民主的失败。因此,虽然以色列的建国宣言采用现代国家通用的平等和民主措辞,宣布“不分信仰、种族和性别而在全体公民中实现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保证宗教和良心自由,以及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但同时又在其《基本法》中确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否认此点者将被剥夺参加国会选举的权利。
在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又是通过一系列与圣经中上帝的应许相配合、神迹般的军事胜利达成的。在这一点上,犹太人不断加强希伯来圣经的弥赛亚式神学意象,而要从中敷衍出民主的主题实在太困难了。在这一点上,以新教为背景显然比犹太教容易建立民主议题,从希伯来圣经出发,基本上只能走到耶稣断然否认的军事性弥赛亚。以色列的现代国家,在气质上也近乎敌视罗马帝国统治的奋锐党,在那里没有余地建立一套关于平等和民主的历史叙事,得到更多保存和强调的是关于大屠杀和六日战争的记忆(好像马萨达和马加比一样)。随着巴勒斯坦人不断加剧的起义,在一个以色列国家之下给予不同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叙事越来越无法找到落脚之处。
当其他国家努力进行世俗化和理性化,而又在其间建立世俗宗教、重塑普世性的时候,犹太人则借助于圣经资源和单一民族统治构建自己的国家历史叙事。这就是现代以色列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植根于国家建设进程及其所依赖的历史叙事,并由此反映在了许多以色列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对犹太人而言,历史研究和国民教育绝对是严重的国家政治问题。因此,从希伯来大学起头,以色列的所有大学都设有两个历史系,一个是“历史系”,另一个则是“犹太史学和社会学系”。或许,桑德教授出于历史学家“追求真实”的责任感,反驳以色列国家的官方历史叙事,揭示了“犹太民族历史”是“被发明”的。本书出版以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各方面的火力打击,作者则对此泰然处之。但无论如何,所讨论的议题注定了本书不得不超出寻常的学术活动领域,而进入广义的政治范畴。或许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本来就是政治的动物,人必须参与政治以实现其本性,而写作、阅读和思考都可以成为人参与政治、实现政治责任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