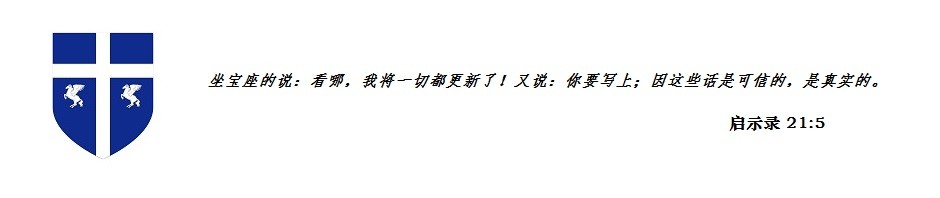甘肃灭门案,惨绝人寰,但是,没出路。
因为,这是个媒体事件。或者说,这个事件必须今日的媒介为载体,事实上传播方式已经决定了结局。跟那许多已经发生过、将来要发生的媒体事件一样,开始碎片化、被人消费,继而开始迷惑,最后被遗忘。或许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人会重提此事,但你会觉得这件事好像已经过去了十年。
为什么?
媒介迫使我们丧失了真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杨改兰,没有一个人了解她的恐惧、愤怒、绝望,也没有人了解她内心的黑暗,更没有人了解她的快乐、她的盼望。然而,当这个案件作为媒体事件呈现的时候,造成了一种“媒体事实”,这个事实又迫使每个人作出道德判断。于是,每个人基于媒体所提供的“真实”,将自己代入某种处境,试图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
随后,我们会发现,“媒体事实”是飘忽的、不确定的。我们手里拿了一个大洋葱,开始剥,一边剥一边流泪,以为正在不断剥出真相,到最后,剥完了,并没有一个内核,我们的泪水,也只是泪腺受到化学刺激的产物。
我们丧失了真实,因为媒体提供的乃是一种“次等真实”(secondary reality,这是沃格林的说法),在次等真实中,没有坚实的基础去做道德选择,而当我们因此漂移的时候,原本确定的道德感也随之摇动。有一瞬间,我们会惊讶于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道德的人。塔西佗冷静地表示,在专制统治下,人没有好的选择,要么屈服而懦弱,要么反抗而鲁莽。在媒体制造的次等真实中,人也没有好的选择,要么作出一个不牢靠的道德判断,要么拒绝作道德判断,而这两者,都损害我们的道德。在次等真实中,我们所作的道德判断,并不是为了杨改兰,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出某种道德品质:爱、正义、智慧,于是,我们就被塑造成为一个伪君子。
糟糕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所面对的“众人”,本身也是一种次等真实。那许多的人,我也并不认识,然而我觉得有义务在朋友圈转发、评论、点赞、拉黑,由此塑造一种“群体”的感觉——我不是孤独的,我从属于一个群体,我被群体认同。这是一种怎样的群呢?——微信群?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真实性又在哪里呢?
清末,西学东渐,康梁改制,造出一个“群学”。在康有为的课纲里,群学与政治学、政治史、政治的运用一同归入“经世之学”。梁启超在《说群》中论“群术”,所追求的效果是“使其[民众]群而不离、萃而不涣”。换句话说,这是一门“共同体学”。必须有共同体,有真实的共同生活,有真实的纽带,才可以形成治理的结构与实践,也才可以有道德判断。后来“群学”一词被严复用来翻译“社会学”,失去了原初的意图。(请参:“当社会学淹没了群学”https://alberttzeng.wordpress.com/2013/06/14/qunxue_shehuixue/。)
路加福音12章,耶稣对门徒论不要忧虑,这样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31-33节)
耶稣讲,你们是一个“小群”。中文的“群”字用得很妙,因为原文也是指羊群。一群羊,聚在一起,要有共同生活。但是,这个共同体又必须有一种良好的治理,治理就意味着政治。这个群的基础,在于政治,而这个政治,必须从上面来,而不是从世间来。所以,门徒必须首先“求他的国”。然后,才能开始作出真实的道德行动,去从事慈善事业。这意味着,要首先有一个更大的真实(truth),比世间的真实更真实,是对抗一切“次等真实”的真实。耶稣说,那真实,是看不见的神国,不是每五秒钟你就要看一眼的微信群。
当然,次等真实也不是没有真实。当第一次得知这个惨案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心中涌动着强烈的情感,一种战斗情绪,想要去与世间的苦难、不公、罪恶作斗争。不过,我们已经无处战斗,也无以为战。我们丧失了战斗的目的、对手和方式(这个主题大得很,得另开一篇)。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腔热血,没有可供投奔的延安,没有可供拼杀的战场,今日,甚至连一片可供被碾压的广场都不会再有。转发过,被删,发图片刷屏,就好像是一种战斗姿态,我们如此战斗过了,洗洗睡,明天继续钻进格子间,瞪眼看看房价,叹一口气,过中秋节。
我写这些有用吗?没用。我无非也在利用这个媒介,有人点赞我会高兴,涨粉我会开心。《魔鬼代言人》里,阿尔帕西诺瞪大眼睛说:Vanity, is my favorite sin。
你必须有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才能与这个越来越诡诈的世界作战。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