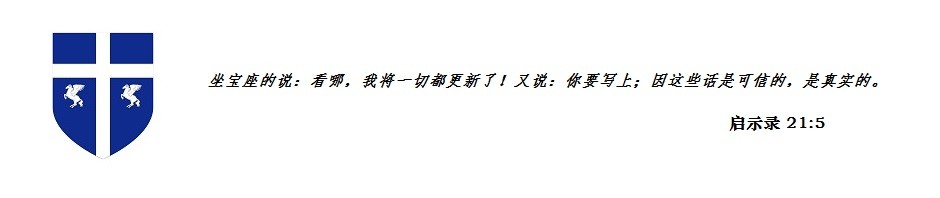与早先的时代相比,现代人对时间的感受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自钟表发明以来,人对时间的感受日益均质化。时间成为一种可计量、可分割、在每一点上同质的流体。这种时间与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这类东西匹配得很好,前一秒和后一秒是一样的,不断往前流动,随着机器的开动,以匀速的方式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工人在这种时间中接受“元规训”,生命也是均质的,因而丧失意义。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注定了人的无聊,时间如冥河之水,静静地流淌。
从荷马到希罗多德,无论史诗还是历史,其功能都是记忆,拒绝遗忘,记下那些不朽的功业,记下英雄的荣耀。这意味着,时间并不是均质的,某些时刻,因着某些人的某种行动,具有更高的价值。基督教传统,也有类似之处,圣徒通过圣洁的生活、与恶魔的属灵战斗、在灵修中与上帝的交通,赋予某些时刻更高的价值。
现代人,或许只有在战争中才有机会直接体验这种异质的时间。
《敦刻尔克》没什么情节,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描绘正面的战斗,甚至都没有深入刻画许多个人物。
要点在于时间。
从一开始,“时间紧迫”的气氛就笼罩住了所有人,背景声中滴答作响。两位年轻士兵抬着担架要赶上船,飞行员计算油量,月光石号的准备和起航,无不争分夺秒。迫降在海上的飞行员无法打开舱门,藏在搁浅船只中的士兵等待涨潮,飞行员小哥决意不返航继续战斗,援救泡在油料中的落水者,时间都变成生死攸关的因素。在这里,一秒钟不再意味着一个汉堡包,而是一个甚至无数个生命。
时间线短暂地交错,好像地壳运动,一个人的时间插入到另一个人时间的下方,交叠、推挤、破裂、结合。你能感受到这种时间的运动充满张力,因为那关系到生死。飞行员的决断、老船长的沉着、少年的死亡,在这样的时间冲突中,才有价值和意义,才产生出各种美德。
也只有在异质的时间中,旅程才有意义。
由于高速交通工具的发明,现代人的旅程被缩短到一天以内。在这样的旅程中,人更像是货物,被塞进一个大铁罐子,不舒服,但知道不久就要结束,于是就忍耐,或许,通过看电影来“打发”这均质的时间。均质时间下的旅程,没有家乡,也没有圣地。
奥德修斯回乡经过艾艾埃岛,同伴们被魔女基尔克下药,“迅速把故乡遗忘”,变作只知吃喝的猪。人陷入均质的时间,失去旅程的目的,唯有战斗方能解除魔咒。《埃涅阿斯纪》中,埃涅阿斯流落到迦太基与女王狄多相爱,类似地危及旅程的目的,最后抛下女王才得以继续建立城邦的行程。Patria,原本是指故乡,本乡本土,一村一城,后来演化成“祖国”。一个人若无故乡或祖国,没有一个要回去的地方,旅程就没有意义,他没有理由奋力前行,去对抗一个个关键的时刻。
基督徒在祷告中会遭遇类似的诱惑,会被诱惑为此世的平庸、均质的时间祈求,求健康、求财富、求工作。耶稣说,那是外邦人的做法,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天国和神的义,意味着在某一时刻与上帝相遇,在某一时刻被上帝指着说:你要如此生活,意味着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要奋力回去。
故乡不是一个人独自蜗居的猪圈,祖国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那就是人要奋力回去的地方。
耶稣起初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保罗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现在时候更近了。启示录的末了,审判之主说,我必快来。
努力向前,要回那个更美的家乡。只有等到坐上了那趟列车,与时间的角力才停止,到那一刻,一切都安静了。
2017-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