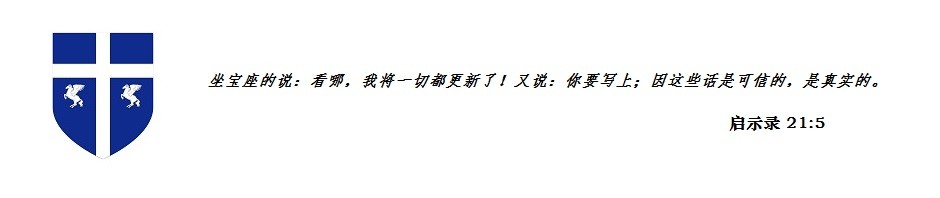李雪莲怀二胎,出主意假离婚,结果丈夫秦玉河趁机另娶。这个哑巴亏着实吃得太大,自己气不过,而且在个小城里,被人笑话起来太没面子。一开始告状,是求安慰,是要想办法把气顺过来。这样,就有了一个矛盾,因为法院系统并不提供安慰。按照法律规定,李雪莲毫无胜诉的余地。法官公事公办,走完程序,证据确凿,就案件而言,毫不复杂,判完了事,合法、干净,不怕上诉。对法院而言,事情处理完了,并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地方。
李雪莲怒气填胸,在气头上的时候想要雇凶杀人,几番运作而不得,渐渐也就有些冷淡下来。中国人最讲“过日子”,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是凡俗的、平常的,只要能过得下去,就可以凑合过。于是,李雪莲决定,只要秦玉河口头上承认当初假离婚,就算了结,虽有诸多不满,也还可以过下去。所以,要去找他。中国人说,这叫找台阶下,哪怕对方不愿给,自己拿块砖垫吧垫吧,自言自语咕哝一句,也就下去了。可是,秦玉河过分。首先,他拒绝私下说话,而原本这是个妥善的台阶。其次,当着许多人的面,指证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又给按上一个“潘金莲”的名号。
这样,事情就严重了。现在李雪莲不只是需要安慰了,她有了一个污名。原本,秦玉河趁机另娶了个发廊妹,有几分瑕疵,但不是处女的指控,反过来把李雪莲的污名坐实了。同时,“潘金莲”的符号,一则指向通奸,一则指向杀人,李雪莲无力反驳通奸指控,又被戳中了暗地里的杀人念头,在她自己的内心,这个标签贴得或许比旁观者认为的还要牢固。
李雪莲本想回归凡俗生活,继续过日子,但被“潘金莲”的标签高高架起在空中,踩不到地面。这个污名,是必须要洗刷的。“潘金莲”的标签一日不除,她就一日不能回归凡俗,不能与人和解尚为小事,不能与自己和解,就断无宁日了。
因此,在本质上,李雪莲的诉求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大半归属神学领域。她需要的不是定分止争,而是罪孽的涤除,涤罪方可使她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重新加入社群。
到这个时候,李雪莲已经被赶到城邦之外,悬置起来,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她所求的,无非是一个人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法院还是没法给她。问题在于,理性化的现代法律无法为李雪莲提供精神上的出路。她去求问过菩萨,后来又求诸于家养老牛,因为菩萨给她安慰,老牛给她洗涮污名。她的这类举动在旁人,甚至在读者看来越是荒诞,越表明这个祛魅的世界能够为她提供的出路着实不多。
然而,有一条夹缝似乎还透出一丝神圣性的亮光,那就是上访。上访跟上法院不一样,法院的修辞是理性化的,上访的修辞是神圣化的。当她上访的时候,或多或少令凡俗生活中表现为符号的“人民”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现实性。而“人民”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措辞,仍然在我们的政治中发挥着可见的功效,是活的,是可运作的。在我们的法官身上,一方面表现为技术性的官僚,一方面却也还表现为“人民公仆”,必须适用另一套修辞。那另一套修辞的境界,是李雪莲的希望所在。
二、朝圣之路
现代国家的治理,诚然表现为一种理性主义下的官僚制,但是,在更深的基底,仍然存在某种神学性的构建。这种构建,往往以叙事的方式表达。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套“建国叙事”,由若干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互相叠加、彼此交错、交叉引用构成。
这类建国叙事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古希腊开始,荷马史诗所述的希腊联军与特洛伊的战争成为一个“叙事之母”,从中孕育了无数的故事。希腊人自然以荷马为先知,而罗马人也把特洛伊的幸存者埃涅阿斯构建为自己的先祖。另一头,犹太人则以出埃及为宏大的国家叙事。到中世纪,欧洲大国依此作法,有联合希腊与希伯来叙事的倾向,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曾表示,本国的王权是特洛伊的余种开枝散叶所致,也表示本民族与以色列史上“失落的十个支派”有关。现代国家的建国叙述虽然貌似不同,但仍然保持了大体框架。比方英国人以“古老宪制”构建一个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的故事,法国人构建一个“自由引导人民”,美国人则有五月花号。
在建国叙事中,“旅程”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意象。开国者历经千辛万苦、坚韧不拔,付出极大的代价,最终到达一个“圣地”,在此开辟出一个新国家。从奥德修斯的漫漫回乡路,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从埃涅阿斯离弃狄多女王,到清教徒跨海前往新大陆;总体上,都是这样一个旅程的叙事。中世纪到近代早期,艺术作品中的“国家之船”形象也都在表达这样一种艰辛、不确定的旅途感。
另一方面,在国本奠定后,需要将建国之初的不安定感转变为稳定的环境设定。因而,建国后期的叙事,就不再以旅程为重点,而是以固定中心场所的仪式为中心。所以,罗马人要有广场,犹太人要有圣殿,巴黎、华盛顿要有按轴线分布的宏大建筑群,供祭司献祭、君王凯旋、人民欢呼。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也具备这一特征。我们有一个“长征”的叙事,强调其路途遥远,一路上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达到了“革命圣地”。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凯旋进城,在北京的广场奠定中心。这个中心是具有国家仪式意义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秩序,表明了国家的秩序,这个空间的失序则是不可接受的。人民大会堂也处在这个空间内,国家仪式会在这里重复排演,这是国家平稳运行的神学基底。
上访,这个举动具有意外的神学意义。
李雪莲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不断脱出凡俗生活,必须寻求污名的涤除。而朝向北京的上访,恰好符合国家叙事中的旅程主题。一个卑微者,走向遥远的圣地,这便成了一次朝圣。
各级官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容易出现错误知觉的。官员们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官僚,负责技术性、日常化的行政事务;一种是国家/人民公仆,具有某种政治神学意义,他们有责任维护国家仪式的正常进行,这恰恰是他们作为“公仆”的责任。对于官员们的期待有两方面,一是要有能力,专业、技术高超,一是要讲政治,意思是,要有“觉悟”(这恰恰是个神学词汇),要“为国家分忧”、“为人民服务”。官员们必须熟悉业务,比如法律、经济,但是又必须熟练运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修辞;他们一方面要接受“数目字的考核”,一方面又必须通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措辞来建立自己的身份。正是这两种身份的混杂,造成了官员们的错误知觉。
李雪莲的情况是麻烦的。麻烦在于,她的案件在法律上毫无理由,在技术性的层面无法获得支持,但是,她涤除污名的诉求,却有某种正当性。同时,上访这一朝圣行动背后的叙事,又能够与官员身份中神学性的那一面对接。“人民公仆”在理论上不能对“人民”采用强制措施,这将危及公仆们自身的身份建构。而兼有二性的官员,在日常中常常难以觉察这类神学意涵。出于技术性的理由,他们直斥李雪莲为“刁民”,这样更加重了后者的悬置状态,提供了继续寻求涤罪的动力。
本来,李雪莲的上访也少有成功的机会,然而,误打误撞之下,她居然混进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更关键的是,她闯进会堂这件事,被领导人知道了,非但知道,还在开会的时候讲了起来。
这个开会的场合,正是重要仪式的执行。仪式的关键,在于行礼如仪,在于规范,在于按照事先排好的秩序进行,任何脱出常规的事件,都将动摇仪式所建构的稳定性。领导人执行的仪式一切正常,直到他提起李雪莲,顺便发了一通火,其中的修辞,都是富有神学意涵的“国家/人民”措辞。事实上,他只是偶尔提到,因为李雪莲闯入大会堂着实离奇。但是,由于仪式常规被打破,就变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最终导致一路官员被撤职。
但是,由于秦玉河不通情理,李雪莲的污名依然未得洗刷,于是她还要上访。官员被撤职,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这个朝圣之路,她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足够长。到这一年,她准备与自己和解了,不需要人来涤罪,牛也可以。然而,官员们的态度最终再次把她推上了朝圣之路。因为,他们“不相信”她。因为,二十年的上访,令李雪莲在官员那里有了另一种“污名”——专业访民,那是不值得信任的。
于是,一场斗争开始了。官员们要阻止李雪莲破坏国家仪式,但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政治神学层面,他们都无法为后者提供救济。官员们曾经握有一个机会,李大头,这个旧情人有可能将李雪莲拉回凡俗的生活,并且几乎成功。在这个计划功败垂成之后,所有人都不得不奔向北京,盼望着在圣坛前的了断,盼望秩序的恢复。
三、沉重的肉身
回头来检视一条线索:身体。
李雪莲看似偶然地脱出凡俗生活,起因是逃避二胎罚款。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鼓励二胎,都是国家对私人身体的“宏观调控”。李雪莲假离婚,借助合法的离婚证逃避国家政策的规训。于是,她的身体就成为一个焦点,形成了一场国家与私人争夺身体控制权的斗争,身体也就不仅仅是物理的身体,而是在反复的抗争中不断转变为“政治的身体”。
李雪莲离婚时还是少妇,按照小说的描写,身材相当火辣。她首先尝试的,是把自己的身体转变为一种资源,比方跟屠夫交换去杀人。李雪莲在这个棋局中缺乏资源,肉体似乎是唯一能够想到的筹码。此时,她的身体更倾向自然身体。自然身体在运用过程中,天然地带有一种下降进入凡俗生活的态势。然而,当秦玉河指控李雪莲为“潘金莲”时,她的自然身体就有了污名。于是,在日益脱出凡俗生活的过程中,李雪莲的政治身体不断增强,而自然身体衰落。
在朝圣路上,禁欲是汲取神学-政治力量的途径,这个因素又与建国叙事中革命者的禁欲因素相通,赋予李雪莲一种神学上(而非法律上)的正当性。在二十年的上访之后,原本青春动人的肉体,变作一副肥胖臃肿的皮囊,却蕴含了更大的政治力量,肉体虽然朽坏,精神却日渐高升,时刻准备好向国家仪式的中心飘动。
官员们几番折冲,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关系却日益激化。官员们的对策,始终偏在控制自然身体的一边,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派警察守住李雪莲家的门口,将自然身体限定在土地上。这个策略后来失败了。
深谙政治之道的市长比下级更有见识,他(至少是直觉地)认识到,最终需要控制的是政治身体,而不仅仅是自然身体。然而,李大头通过肉体的欢娱对其实施招安的计划最终失败,李雪莲因为身体的圣洁被破坏而再次决然地踏上涤罪朝圣之路。
不过,在这最后一次朝圣途中,很快揭示出朝圣者实际上并没有两个身体。当自然身体日渐衰弱,政治身体也就无从依附。相比二十年前的荒诞喜剧,这一次朝圣变成了苦路之旅。李雪莲在昏迷中被送进卫生院,那同样是现代国家喜闻乐见的身体规训场所。朝圣者的身体并未被家乡的官员控制,却被异地的医生掌握。医疗费,意味着李雪莲又不得不下降,进入凡俗生活。她被救护车送进北京,却是望广场而不得入,为了解决医疗费艰难地寻亲。
这一次,李雪莲是被迫回到凡俗,官员们没有做到的,医生做到了。最后,官员们前来报告秦玉河的死讯,撤销了李雪莲涤罪的现实途径,这个朝圣者,她的政治身体,终于被宣告死亡。
我认为,事实上,这里才是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李雪莲的政治身体被宣告死亡后,她的自然身体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那一刻,她的整个身体都遭到了消解。她在悬置的状态中,突然被抽去了神圣性,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掉落回凡俗,却发现,世间已然无处安放肉身。官员们看守着这具奄奄一息的身体,坐等国家仪式施行完毕,打道回府。李雪莲,最后,上吊被果园的承包户阻止,最后的最后,她的身体不知所终。
就这样,结案。
四、麻将与肉汤
小说令人动容之处,在于李雪莲长长的故事只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最终突入一个无解的死局,而短短的“正文”要解开这个局面。
昔日的县长史为民,因李雪莲上访被免职。事实上,老史完全有理由上访,比李雪莲硬得多。然而,他却与生活达成了和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桌麻将,一锅肉汤。
麻将不可以是赌钱的麻将,而是四个朋友的麻将;肉汤不可以是普通的肉汤,而是极致美味的肉汤。
老史靠着祖传肉汤秘方,开一间饭店“又一村”(这句诗是极好的),每天只煮两锅肉,远近闻名。他不贪心,只是靠此衣食无忧。再有三个好友凑成一桌麻将,生活比县长舒服。
老史无须上访,因为他主动地重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凡俗生活,而且,还是极度滋润的凡俗生活。所以,当他在北京滞留,听说牌友病重,要赶最后一场麻将,就举起访民的牌子,自愿被遣送回原籍。
这个表面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一种“逆向”的朝圣之旅。老史能够利用和操纵悬置的神圣生活——上访,并带着微笑将之平稳地带回地面,消解一切张力,继续并加强了自己的凡俗生活。
这大约就是所谓中国人的智慧,大约是作者提出的破解死局之道:麻将与肉汤。中国人,有一锅肉汤喝,有一桌麻将打,足够过日子,而且过得很安逸。
问题是,如今,我们去哪里安放这一张安静的麻将桌?去哪里找到一帖肉汤秘方,得以进入那舌尖上的中国。序言和正文,哪个是魔幻,哪个是现实?
五、法律的困境
最后要谈谈法律的困境。
在整个故事中,法律的地位极为边缘。原因相当明显,中国的法律,向上不能连接到国家叙事,故缺乏神圣性;向下无力提供凡俗生活,因而难有群众基础。
西方传统,法律有天然的神圣性,各国的建国故事,多半有法律的因素参杂其中。犹太人的国家由上帝直接颁布律法;希腊有半仙样的哲人立法;美国,清教徒在船上就已经立了公约,嗣后大法官取得了近乎大祭司的地位;英国,大宪章几乎成为神话;法、德,各以法典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如果法律参与建国叙事,就自然能扮演神圣性提供者的角色,中国没有。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凡俗生活,又并非建立在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之上,甚至美食在这个关节点上的功能都要强过法律。
于是,法律就只能发挥机械的功能性,成为官僚制中的一套齿轮。这套齿轮的运行,会受到从上面来的神圣性的干预,也会受到从下面来的凡俗性的影响。在李雪莲的案子中,法院完全缺乏应对能力,依法裁判的结果是“对人民漠不关心”、“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同样,法院也无法给李雪莲提供一种喝酒吃肉打麻将的凡俗生活,“上法院”总是没好事的。
因此,中国的法律和法学,大概被夹在上下层之间,却又不能承担沟通上下层的任务。除了埋头把齿轮擦擦亮,把一个齿轮组分解为若干个齿轮组,或者不断增加新的齿轮组之外,并无他法。
法典,自然是被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为按照设计,它应该有向上连接神圣性、向下提供凡俗生活的功效。“应该”这个词表达虚拟状态,或许,直到法律能够讲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虚拟才会变成现实。
2017-07-25